辣评蒋介石,怒怼宋子文:陈光甫的日记里,藏着一个“毒舌”评论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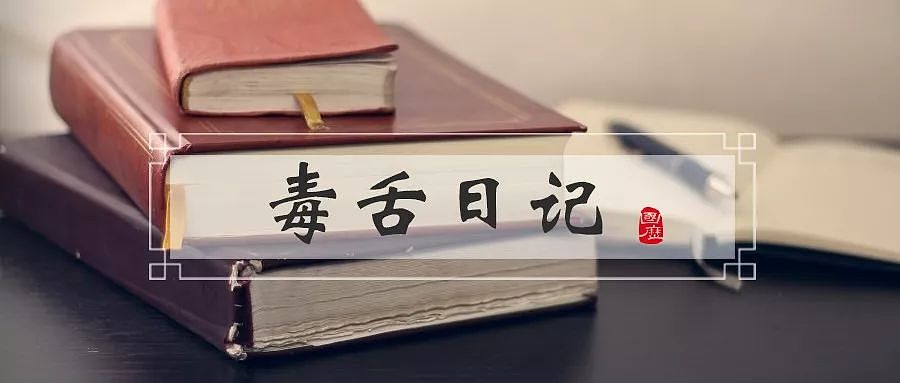
本文为“国家人文历史”独家稿件,欢迎读者转发朋友圈 文章有删节
“昨夜九时乘日清公司瑞阳轮船赴汉,今早八时半舟始启碇,因候潮水也。临行承敦甫、淞荪登舟相送,殊为可感。”1928年1月9日深夜,于瑞阳轮特别舱搭乘轮班的陈光甫颇为寂寥,在日记簿上写道,“今日天气不佳,十一时出吴淞,风浪大作。舟中无事,看书消遣”。
文中的“敦甫”即杨敦甫,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总行副经理,也就是总经理陈光甫的第一副手;“淞荪”即贝祖诒,时任中国银行上海分行经理。这二人前来送行非同小可,证明陈光甫离开上海寓居武汉的时间将非常长久,因此临行前已将上海银行的主要业务交托予杨氏,并委托贝氏从旁协助。

陈光甫
武汉当然也是陈光甫的旧游之地,事实上,他虽然籍贯江苏丹徒,但就事业履历而言,算是“半个”武汉人,其青少年时代就在这里度过。在离开上海前夕他是向上海银行管理层打过招呼的——对外的公开理由是处理其父在汉口的遗产;而对内的秘密理由是,上海银行汉口分行经理唐寿民刚刚辞职,他要去清理账目。但无论怎么看,这两个理由都不会令其在武汉滞留大半年之久。
就在五六天前,也就是1月3日,南京政府明令宋子文接任财政部长,在财务金融方面为即将复国民党军总司令职的蒋介石作铺垫。或许,蒋宋的重新崛起,才是陈光甫畏避汉口的真正原因。
蒋介石是“七成张作霖”
陈光甫很不喜欢蒋介石。早在1927年6月11日,也就是蒋氏占据江浙沪不久,陈光甫在私人日记中,对其人就多有讥评。
当时国民党因内部分裂,北伐差不多停了下来。国内颇有势力的军政力量分成四块:国民党方面的蒋介石集团和汪精卫集团,以及北洋方面的张作霖集团和孙传芳集团。对于北洋系,陈光甫认为其已经失败,并在日记中分析了原因。他认为,“孙到江浙一事未办,以致失败”,也就是说孙传芳没有为辖区人民办好事谋福利,以致失去了群众基础,没保住江浙地盘。
至于张作霖当时虽然还盘踞东北华北,但陈认为他也失败了,并总结了原因:一是“不恰舆情”;二是“滥发奉票,以之扩充军备”;三是“不善用人”;四是“不代人民做事”,五是“以个人为本位,视东三省如张家天下”。
然后他断言,“蒋之政府成立时间虽尚早,不觉已有七成张作霖之办法”。具体内容,陈也总结了三条:一是“不顾商情,硬向中国银行提款一千万元”;二是“以党为本位,只知代国民党谋天下,并不以天下为公”;三是“引用一班半无政府党之信徒扰乱政治”,这里的“半无政府党信徒”指的是那些身为国民党元老的前无政府主义者李石曾、张静江,他们经常提出一些不切实际的宏伟蓝图,令执行者啼笑皆非。既然蒋介石“已有七成张作霖之办法”,那么,在陈光甫眼中,蒋氏也就已经败了七成。
不过,陈光甫心里也知道,蒋介石乃至国民党的走向,不仅仅其个人选择或政策选择,其背后还有一个关于“革命”走向的意识形态问题。比如“以党为本位,只知代国民党谋天下”,这对于蒋氏而言,“党国”非但不是问题,而且还是政治目标,这让他如何修正?
对于国民党及其革命来说,陈光甫也算是故人。1904年夏,作为湖北省政府派遣的“赛品员”(职务名),他参加了在美国举行的圣路易斯世界博览会。在现场他结识了正好于北美游历,以洪门当家身份在华侨中鼓吹排满革命的孙中山。
他拒绝了孙投身革命的邀请,但愿意掏出口袋中5美元资助以表达自己的倾慕之情。他还告诉孙,在法德有一批湖北籍的留学生已经形成革命团体,并正在寻找孙作领袖。这个信息直接导致了孙在年底的欧洲之行,开始了团结吸纳留学生为新目标的革命政略。
在圣路易斯,陈光甫还结识了孔祥熙,后者即将入耶鲁大学进行硕士研究。陈只比孔小一岁,当时已经24岁,但自12岁到汉口当学徒以来,没有受过一天正规教育。他固然因自学英语而考入邮政局,后又因岳父景维行向署理湖广总督端方举荐而成为“赛品员”,但毕竟无论在中西,这都不是功名正途。他非常羡慕孔差不多是自己同龄人却已经成为名校硕士,孔鼓励他临渊羡鱼,不如退而结网。于是,陈在美国留了下来,从高中念起,最后成为沃顿商学院的首位中国籍学生。
自此他同孔祥熙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在私人日记中,他一直称孔为“庸之兄”,示以内心的尊重和亲切。
自美国学成归来,端方已经调任两江总督兼南洋大臣,陈光甫便进入其新创立的“南洋劝业会”任外事科长。迨端方调离,他应江苏巡抚程德全之召任其财政幕僚。据他的好友唐寿民回忆,临行前他们曾商议,“如果革命发动,所需财政从何而来”,遂决定建议程抚将之前属于江苏省政府的官钱局改组为省银行,以便革命发动时党人更方便掌握财政币制。

江苏巡抚程德全
此时正好辛亥革命发动,程德全成了新政权的江苏省都督,陈光甫也乘便以财政司副司长的名义成立江苏银行,自任总经理。这一年他才30周岁。两年后,国民党发动反袁革命,陈以江苏银行名义给陈其美、蒋介石支付了大量军费,被当局侦知,引起了袁世凯震怒。幸好袁的秘书张一麐从旁缓颊,袁才收回了已经签批的格杀令。
经此风波,陈光甫在官办银行业待不住了,于是辞职创办上海商业储蓄银行。那颗之前躁动不安的革命之心,也渐渐淡了下去,不复再成为人生选择。
直到12年后,他又遇到了还打着“革命”旗号的蒋介石。
唐寿民“勾结宋子文”
蒋介石毕竟是个军事领袖,平常同金融家接触很少,陈光甫即使厌恶之,倒还有回避的余地。但宋子文就不同了。其人在北伐前后完全就是国民党的“钱袋子”,其左倾的政治倾向也使得他更乐意以政府之手来干涉和操控银行界的市场运作。
而且,宋子文同陈光甫还有些旧仇新怨。两人其实历史关系很深——贝祖诒的父亲贝理泰既跟陈光甫关系密切,也跟宋子文的父亲宋耀如是好友,宋、贝、陈三家算是世交。20世纪20年代初,宋子文在上海开设商号,进行金融投机,请上海银行为其开立限额为50元的往来透支户。没想到陈觉得宋少年浮浪,为人不稳,竟然一口拒绝。
到1927年,宋子文身为革命新贵,挟北伐军的雷霆之威来到武汉,要求各大银行报销军费,不料遭到集体拒绝。晚间,上海银行汉口分行经理,也是陈光甫的老友唐寿民私下找到了宋子文,他说道:“今天的会议其所以无结果,主要是没有一家银行敢于出头露面,先行动笔写认若干。凡事必须要有个始作俑者。希望你明天再次召集各银行开会,由我来先写。因为上海银行是一个商业银行,过去对各项捐款比例很小,尤其是军政界借款,上海银行从不参加。如果由我先动笔,同业必然大为惊诧,也就不便推诿了。”

宋子文于财政部长任内
宋子文听了非常高兴,依计而行。在新召集的会议上,唐寿民一提笔就写了“认捐二十万元”,参会的各银行经理,尤其是中交两行的汉口负责人大惊失色。但事已至此,不得不随声附和,其捐款均高于20万元。唐寿民这一行为得到了宋子文的好感和信任,却激怒了陈光甫。他立即让唐回上海总行述职,痛骂其如此重大事件不经请示就擅自行事。唐面子上吃不消,当场拂袖而去,自立门户。
次年陈去汉口住了大半年,想起此事还积郁难平。在私人日记中,他竟滔滔不绝开列了唐的七大“罪状”。比如第二条就是“在职之时不知节省,家用、外用非分扩张,以致不安于位。在行领俸之时,就要去勾结宋子文,故外间谣传已派为厘金总局长等语”,然后下了个结论:“此之谓不忠。”陈光甫还在日记里感慨道:“汉行为何没有第二个人可靠?”他甚至觉得“一种黑暗之气笼罩全行,或云腐败气亦可”。
其实,同“革命”新贵宋子文勉力周旋乃至竭诚报效,唐寿民的出发点应该是为了上海银行的利益。当然,为此得到了宋的青眼有加,也是副产品。后来,也正是这层关系,他担任了交通银行总经理、中央银行常务理事等重要职务,成为民国金融界的头面人物。
在汉口大半年,唐寿民的“背叛”一直让陈光甫十分气愤。在同时间和学生伍克家的通信中,他又说起唐寿民,“由江苏银行月入十数元起,至每月收入八千余元,到汉后竟急急要东做生意、西做生意。若说其有意害我,则我不敢信;但是他为何要如此做法,为何还不知足?此无他,乃受镇江环境式之麻醉也”。“镇江式”是陈光甫自造的概念,他曾在日记中解释,“为领袖谨惕者少,思借地位而营私者多”。这顶大帽子扣下来,他全然不顾自己其实也是镇江人。不过,陈光甫眼光确实独到。抗战时期唐寿民落水成为经济汉奸,确实是他爱慕虚荣、热衷投机的再一次表现。
陈光甫不仅在事务上同宋子文多有龃龉,其对宋的人品也多有不屑,认为其“为人毒辣,不讲情面”。1928年初,随着蒋介石复职的呼声甚嚣尘上,陈光甫已然萌生退意;到南京政府明确任命宋子文为财长,陈也就只能一走了之了。
“中国受中亚细亚民族之影响甚深”
自1928年陈光甫提出统一币制,到1935年法币改革,其中相差了整整7年,其中宋子文的迁延拖沓达5年之久。在陈光甫日记中,也揭露了宋的这种颟顸误国。他写道:“中国不肯马上脱离银本位,即是恐怕力量不足,觉得非一笔大借款无此胆量毅然决定改变币制。此种思想几弥布政府全局,此为延误事机之唯一实情。宋子文主张最力。”
币制改革的无政策、无决策、无对策,以致在宋子文手上5年毫无进展,其人确实难辞其咎,但由于成见过深,陈光甫会很敏锐地捕捉一切不利于宋的负面消息,并深信不疑。比如1932年3月17日的日记,认为宋子文跟蒋介石一样对日坚持“不抵抗政策”;5月3日,又道听途说宋子文向法国购买军火若干,便得出结论“宋有准备自做独裁之势”,“此人要做军阀”。
当然,宋子文对上海银行也不友善。其母倪桂珍是上海银行的最老股东之一,其私人存款也长期存放在该银行。倪去世后,等这些存款一到期,宋马上全部提取,存入外资大通银行。这笔款项要近十万元,如此全部提清,很显然是对上海银行的不信任。难怪陈光甫要恨恨然地“特将本票摄影保留,籍资日后参证回忆”。然后在日记里他直接评论道:“窃思华人对于本国金融不知爱护维持,又何能苛责外商银行之言行不相顾哉?”
陈光甫之于宋的恩怨,二十年如一日。1947年4月23日,陈作为国府委员参加成立会,遇到了宋子文。据当天日记,宋子文笑着对陈说:“你简直是个妖怪,真不像有六十七岁的人。你究竟有一个怎样的秘诀?”陈笑答道:“没有别的,也许还是我一直不做事的缘故。看你如今官不做了,神气也很好啊!”
此时宋子文刚因“黄金风潮”从行政院长位子上下台,举国笑骂,陈光甫再去补上一刀,实在是没有必要。不过这也证明他对于宋子文的偏见,从未消除。
对于李宗仁他也一直保持着好感。虽然两人后来也没什么接触,但直到1949年,陈光甫在私人日记中依然尊称李为“代总统”。
不过,对于其他一些社会问题的思考,20年来,陈光甫却有着绝大的变化。
1928年初,他决意自上海退居汉口的时候,由于心情恶劣,也由于此地刚经历兵灾,尚未恢复,反正,陈看出去,是一片混乱衰败,到处是所谓“穷化恶化”的证据。在此时的日记中,他认为中国需要欧美管制,因为“乃有英美等白色种族优秀分子在内,有移化之力,故可常新不坏”。他还认为,中国消极不振的原因是“数千年亚洲遗毒”厉害,所谓“中国受中亚细亚民族之影响甚深”,无法“善化”。
但是,20年后他履迹香港,却又是另一番感观。1948年12月7日,在日记中,陈光甫由衷地说道:“吾四十年以来游历中国地方不少,不必谈西北、东北、广东等处,即以苏北而论,姜堰、曲港、通州、大中集,均系富庶之区,地方平安无事,人民安居乐业、从事生产,较之香港,有过之而无不及者。不过香港在物质上比较近代化一点。”竟然把这些苏北小镇的安和乐利同香港相提并论,可见他通过这20年看到了中国的演化和进步。
至于对待蒋介石的态度,陈光甫一直保持着高度的冷静和冷漠,对其很少有个性化的评论,也不用任何尊称,难得呼之以职衔。到1947年4月23日陈新任国府委员,可能是因为感激之情吧,于日记中开始尊称蒋氏为“先生”。当然,对其施政方针还是批评,认为“要继续打内战,国民党已经没有这个能力”。他十分形象地揶揄道:
“今天的政府好有一比,所谓三句话不离本行,国民政府正如一家银行,国民党办了二十年没有办好,生意做差了,或是不能兑现,或是怎样,这家银行岌岌可危,于是总经理蒋先生不得不去拉些新股东来——或者比传的更确实些——请几位新董事而总经理不变,希望因为这些新分子而银行可以暂渡难关,依然维持下去。”
从此以后,他私人日记中,“蒋介石”就变成了“蒋先生”。但这位“蒋先生”在大陆的末日,也即将到了。
更多精彩内容,欢迎点击卡片进入“果粒时刻”小程序阅读
喜欢本文的各位,欢迎转载到朋友圈









 +61
+61 +86
+86 +886
+886 +852
+852 +853
+853 +64
+6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