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女作家再失爱子,7 年前,她的大儿子自杀(组图)
2024年2月20日,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在学校官网发文披露,该校学生詹姆斯·李在学院路交叉口被火车撞倒后身亡,年仅19岁。

这位普林斯顿大学大一的新生才华过人,精通日语、西班牙语、意大利语等多国语言。
他的母亲李翊云是继哈金之后,在西方文坛上第二位以英文写作而名声大噪的华人作家。
 ● 李翊云
● 李翊云
李翊云曾在2021年的一场对谈中谈到自己的小儿子,说“他特别喜欢看《三体》,特别喜欢看刘慈欣,也看刘宇昆的作品,还有特德·姜。他不会看我的作品,会看经典的侦探小说,比如《福尔摩斯探案集》。”
令人唏嘘不已的是,7年前,李翊云的长子文森特就因自杀身亡。如今,年过半百的她再度遭遇丧子之痛。
熟悉普大环境的学生强调,列车经过学院路口时,通常都会有响亮的警示声,一般行人很难撞上火车。
因此,有人推断,李翊云的次子也是自杀的。
 ● 李翊云和两个儿子在一起
● 李翊云和两个儿子在一起
再向上追溯,李翊云本人也曾因为严重的抑郁症而两次轻生。
当死亡的魔咒施于这个本应幸福的家庭时,我们似乎更想探寻悲剧背后的故事与肇因。
1.移情“缪斯”
“把美好的东西毁灭给人看”的悲剧感往往是在强大落差下产生的。如果翻开李翊云的人生履历,我们会惊叹于她的光环如此耀眼。
1996年北大生物系毕业后,她远涉重洋到美国爱荷华大学攻读免疫学,并在2000年获得硕士学位。随后,她放弃了即将到手的免疫学博士学位,转而从事写作。
2010年,李翊云获得美国“麦克阿瑟天才奖”。“麦克阿瑟”基金会的评审认为,李翊云的英文写作反映出其母语的语调及文化,这给英文读者带来一种别开生面的体验。那一年,她还上榜《纽约客》“最值得期待的年轻作家。”
短短两年后,她成为了第一位荣膺欧·亨利奖的华人作家。

2013年,李翊云受邀担任第五届“布克国际文学奖”评委;2020年,李翊云因作品的“形式美和大胆的想象力”而获温德姆·坎贝尔奖和古根海姆奖。2022年,李翊云入选美国艺术与科学院院士,一年之后,她又凭借新作《鹅之书》获得福克纳文学奖。
因创作成就斐然,李翊云被认为会是第一位获得诺奖的华人女作家。
但她小时候从来没有梦想过会成为一个作家,尽管对文学的热爱就像天然的基因一样深植于心。
和同代人一样,李翊云成长于阅读资源颇为匮乏的环境中,她如饥似渴地阅读任何可以得到的文字,包括“鱼贩不要了的旧报纸,连环画上的高尔基自传三部曲,托尔斯泰《复活》的报刊连载,图书馆借来的屠格涅夫的《散文诗》”,此外她还大量阅读英美文学巨擘狄更斯、托马斯·哈代、D·H·劳伦斯、海明威等人的著作。对于中国的古典诗词她更是如数家珍。

读书为她暂时屏蔽了周遭的种种难堪与烦恼,甚至让她挺过了那些充斥着家庭暴力的岁月。
虽然醉心文学,李翊云上大学时却选择了一个与她的兴趣大相径庭的专业。
到美国深造后,她将成为一名业界专家的方向清晰可判,连人生的道路似乎也一眼能望到边,这种没有任何挑战的确定性让她对未来产生了怀疑。
读硕士时,因为实验任务很重,大家纷纷寻找减压的方式,不少同学选择了园艺来解压,李翊云却报了一个社区写作培训班。
在那里,她发现了自己对写作的浓烈兴趣,于是决定离开科研,尝试英文写作。
她的高中同学对其予以劝阻,“我不相信你能写成,你在中国长大,你怎么去写美国的上层和主流社会?”她的丈夫也提醒她,比起科研,写作对她的索取会更多。但她“去意”已决,告诉丈夫,给自己三年时间——如果三年结束,写作还没进展,她就去读MBA,或法学院。
2002年,李翊云在The Journal杂志上发表散文《充满蝉声的夏天》。2003年,老牌文学期刊《葛底斯堡评论》发表了她的散文《那与我何干?》。那年的秋天,她的小说《不朽》被《巴黎评论》在自由来稿里选中,被赞誉为“一篇堪称完美的小说”。
《巴黎评论》的编辑布丽吉特·休斯在采访她时说,发现李翊云的写作才华,是比自己当上《巴黎评论》的主编更令人兴奋的事。
2.“我有信心扮演我的存在”
在英语文坛一鸣惊人的李翊云很快就成为了媒体广泛关注的对象。2004年,她获得了《巴黎评论》年度新人奖。权威文学杂志《格兰塔》和《纽约客》也分别命名她为美国最杰出的青年小说家之一。
不久,李翊云考取了爱荷华大学“作家工作坊”。
这个知名的创意写作项目全美排名第一,声名远扬,培养出了17位普利策奖得主、4位美国桂冠诗人,以及众多国家图书奖、麦克阿瑟天才奖得主。
它附属的“国际写作计划”由著名华人作家聂华苓及其丈夫、美国诗人保罗·安格尔共同创办。很多中国作家:王蒙、北岛、王安忆、阿城、莫言、苏童、余华等,都参加过该计划。
在“作家工作坊”的严苛写作训练,让李翊云于2005年获得了爱荷华大学艺术创作硕士学位,兰登书屋很快买下了她短篇小说集的版权,并于同年推出了她的第一本书《千年敬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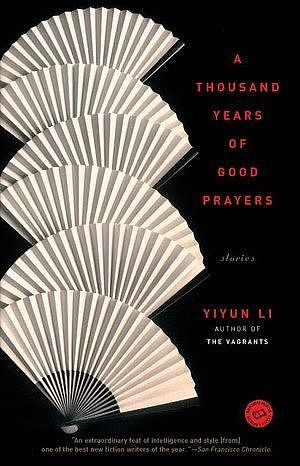 ● 《千年敬祈》(A Thousand Years of Good Prayers)
● 《千年敬祈》(A Thousand Years of Good Prayers)
这部短篇集以90年代的中国为背景,从人潮汹涌的北京、广袤苍凉的内蒙古,一直写到了大洋彼岸的芝加哥,最终摘取了弗兰克·奥康纳国际短篇小说奖、美国笔会海明威奖和英国卫报新人奖等多项大奖。
出任评委会主席的克莱尔·阿米茨泰德称赞《千年敬祈》一书:“她所讲的故事冲击着人们的心灵,即使合上书很久很久,它们仍然在不断地膨胀发酵。”
2008年,著名华语影视导演王颖把《千年敬祈》搬上银幕,俞飞鸿出演了重要角色。
 ● 俞飞鸿主演的同名小说改编的电影《千年敬祈》
● 俞飞鸿主演的同名小说改编的电影《千年敬祈》
继《千年敬祈》后,李翊云又出版了短篇小说集《金童玉女》、长篇小说《漂泊者》。从《千年敬祈》到2014年发行的长篇《比孤独更仁慈》,李翊云这一阶段的作品大多发生在中国,或以中国人为主要人物。她坦言,一个人和母语之间的联系,其紧密程度是超乎想象的。在祖国的成长经历和所见所闻,是她用英语写作的最大源泉。
在布丽吉特·休斯看来,李翊云或许的确为英文世界注入了宝贵的中国经验,但更重要的是她不同于其他作家的特质:“对时间的持久兴趣,对将自己视为独立个体的追求,一种拒绝服从任何期待的执拗,无论这期待来自他人还是她自己。”
因此在旅美华人作家中,李翊云是个无法被归类的“异端”。
此外,她厌恶陈词滥调,反对有章可循的“技法”,抗拒美国写作坊教授的金科玉律。
她了解自己作品的价值,并会坚定地捍卫它们的稀缺性,哪怕被人视作“敝帚自珍”。在修改首部长篇《漂泊者》时,李翊云的编辑凯特·梅迪纳劝她去掉一个年轻女性角色脸上的胎记,她毫不犹豫地拒绝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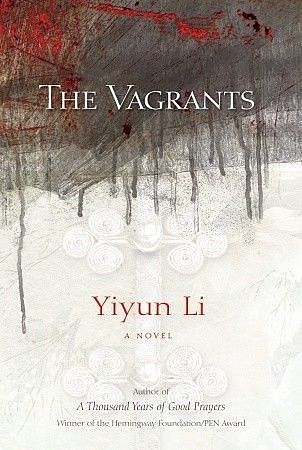 ● 《漂泊者》(The Vagrants)
● 《漂泊者》(The Vagrants)
此后,她不再采纳梅迪纳的建议。梅迪纳是一位资深编辑,与众多作者都有过密切合作,包括南希·里根。面对这位“无法被驯从”的作者,她无奈地对别人说:“翊云不好管。”
李翊云曾在文章强调:“我有信心‘扮演’我的‘存在’。”
有人说,“如何不被低估、如何证明自己大于肉眼所见,是许多移民毕生的需求,也是动力。对用第二语言从事写作的创作者来说,或许更是如此。”
但李翊云拥有自己的底气与自信。迄今为止,李翊云已出版六部长篇小说、三部短篇小说集、一部回忆录,很多作品被翻译成西班牙语、意大利语、法语、日语等十几种语言,她也因此成为用英语创作成就最高的华人作家之一。
3.原生家庭之殇
李翊云的成功被视为海外华人励志故事的样板,但只有她自己知道,她的刻苦攻读、她的出国留学,其实都是为了逃离自己的父母与家庭。
小说家英格博格·巴赫曼曾写过,“我正在用被灼伤的手书写火的本质。”其实这也是李翊云的感受,她的写作讲述了形形色色的故事,关于生存与挣扎,关于冲突与人性的战争,但光怪陆离背后,是她承受的巨大创伤。
李翊云出生于北京的一个四口之家,是家中最小的孩子。她的母亲是一名优秀的教师,受到一代代学生与家长的尊敬,但在家中却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暴君”;父亲作为核物理学家,是母亲经常责骂的对象。“面对骄纵跋扈的妻子,他的应对方式永远是无节制的退让和自我麻痹。”
 ● 1977年,李翊云一家四口合影
● 1977年,李翊云一家四口合影
在两个女儿中,母亲偏爱出色的小女儿,但母亲的忽冷忽热和畸形的爱令李翊云难以喘息。
李翊云说,“很早之前,虽然还无法将其诉诸言语,我就知道:母亲才是这个家中唯一的孩子。比起母亲的愤怒,我更害怕母亲的眼泪。巨婴式的母亲,需索无度。她的占有欲和控制欲失控得几近病态,家中每个人因此都不得安宁。
她说,我,这个她唯一深爱的人,活该得到最残忍的死法,因为我不懂感恩。”
 ● 李翊云(右)与父亲、姐姐
● 李翊云(右)与父亲、姐姐
在一种扭曲窒息的氛围中生活,“出逃”成了一种必然之选,后来当李翊云放弃可以给她带来光明前景的专业,而从事作为“情绪出口”的创作,也源于对长久积压的痛苦的一份宣泄,对人生真相的一种追索。
后来,她在美国坚持用英文写作,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她的母亲不会英文,这门外语于是成为了一道厚厚的“屏障”,将母亲的审视与操控阻隔于外,李翊云也借助这种方式获得了从未有过的自由:
“当一个人用新的语言记忆时,他的记忆就有了一条分界线。在那之前发生的,可能是别人的人生,也可能成为某种虚构。”
她试图通过构建新的语言体系,来摒弃过往,完成自我救赎。
但这个过程非常艰难。
创作期间,李翊云患上了严重的抑郁症。根据《卫报》报道,整整 10 年,李翊云都在午夜到凌晨四点之间写作,还要平衡家庭和白天的工作。她曾认为自杀是“一个合适的、甚至是唯一的选择”。2012年,李翊云两次自杀未果。
李翊云因为抑郁症第二次入院治疗结束后,加入了一个康复项目,然而那些康复项目对于一个心灵受到长期戕害的人而言,显得漫长而微弱。她常常生出强烈的愿望:我要是从未出生过就好了。
李翊云在住院治疗期间,喜欢一个人去花园,沉浸于书籍的世界,一读就是好几个小时。别人觉得她看上去安静平和,不能理解她为何会有自杀这种念头。她说她表面最平静的时候,是内心最激烈的时候。

“天人交战”于她而言,是常态化的内心戏码。面对命运的吊诡与冷酷,她拒绝无谓的妥协与和解。
她想起父亲曾经灌输给她们的宿命论——“只要相信宿命论就会让一个人看起来平静、无所不能,甚至是开心。”这是她当年与姐姐唯一的“护体”。但阿Q式的精神胜利法无法掩盖那些被深深压制的悲伤、无助与绝望,它们的汁液渗透到了每一寸肌肤里,甚至长成岁月的纹理,以至于她后来无论用什么方式,都难以将其彻底清除。
无法选择的出身与家庭,成为她一生都摆脱不了的“宿命”,而这种“宿命”,成为流动的沙漏,最终影响到她与下一代的相处模式。
在李翊云的记忆中,一天下午,她与小儿子坐在长凳上等待大儿子下课,小儿子把手放在母亲的手上,但是她却无法理解:
“我知道那一定很舒服,并且是天下最自然不过的事了。一定是这样的。不过我突然觉得我无法理解它。我能接近理解它,但是那只能是作为人类学家的理解的一部分。”

尽管她笃信,日常的亲密关系比外部的惊涛骇浪更值得书写,但在原生家庭中无法获得健康之爱的“残缺”,让她在自己成为母亲后,也难以做到与孩子真正的水乳交融,因为那种自然而然的亲昵无间、温暖明亮的情感慰藉,是她不曾拥有过的生命体验。
起源于上世纪50年代的“家庭系统心理学”认为,“家庭是一个系统,家庭中的任何事件都会在每一个人身上留下痕迹……爱与恨都能够通过家庭一代代传递。过多的创伤彻底改变了生命感觉,并且在家庭的集体无意识中留下了足以导致更多苦难的阴影。”
2017年,李翊云被普林斯顿大学聘为教授,她准备举家搬迁到新泽西州去。但秋季还没开学,命运却与她开了一个残酷的“玩笑”——她16岁的长子文森特自杀而亡。
 ● 李翊云主持普林斯顿大学的小说研讨会
● 李翊云主持普林斯顿大学的小说研讨会
此前,文森特还随母亲去看房子,“甚至对厨房、花园和他的卧室都有了计划”,但新家还没有搬进去,他就走了。
没有来由的结束,对于活着的亲人来说,像极了突然被推至无底的渊薮。
后来李翊云在书中写道:“我们买了你看中的那幢大房子……你要在就好了……没有你,房子空荡荡的。”
4.生命是一场漫长的疗愈
更让李翊云悲恸的是,不久后她的父亲也患病去世了。在医院里照顾病重的父亲时,李翊云犹豫了很久要不要告诉他外孙自杀的消息。
最终,她还是选择了沉默,因为她觉得父亲已经承受了太多的打击。
她和父亲都不擅长表达感情,直到父亲去世,她都不知道父亲为何总喜欢唱《北国之春》。《北国之春》里有句歌词:“虽然我们已内心相爱/至今尚未吐真情/分别已经五年整/我的姑娘可安宁”,是因为歌里有父亲生前曾渴望的缱绻之爱和家庭的幸福吗?
不得而知。包括对于文森特的死,她同样百思不得其解。
曾经,“她致力于将自己和生活藏在小说里”,儿子去世后,她意识到逃避没有意义,决定以最直接的方式面对儿子之死,于是就有了2019年出版的《理性终结之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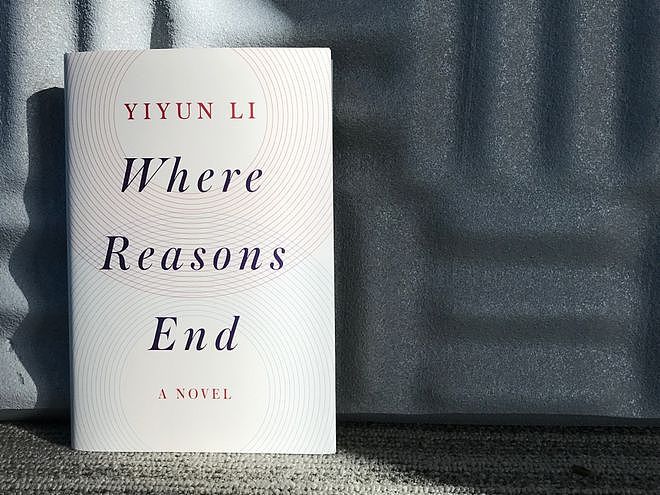 ● 《理性终结之处》(Where Reasons End)
● 《理性终结之处》(Where Reasons End)
畅销书作家伊丽莎白·麦克拉肯称,这本书是“关于世界上最悲伤的事情”。
小说中的母亲特别想知道,一个身姿轻盈如鹿,喜欢阅读、音乐、烘焙,能轻易地用他的蛋糕、鲜花、歌声占满整个空间富有活力的少年,为什么会选择结束生命?死亡究竟意味着什么?母亲是否能够拯救自己的孩子?
在书中,她调动小说家的想象,在时光隧道里,与逝去的儿子进行了一场不可能的对话。
儿子:我非常爱你,希望我没有伤你的心。母亲:哦,别那么说,令人伤心的是生活。儿子:你是个好母亲。母亲:没有好到能使你留下来......
与其说这是一份困惑,一种自责,不如说是一场与自我的对话,一次省察,她希望自己能懂得儿子的选择,就像理解当年她自己的那些行为一样。
即使是在最难熬的时刻,她也习惯性地微笑,“我时不时会停下来听正在吠叫的鹦鹉,它不知道从哪里学来一句,‘那只狗的事我很抱歉!’……所以在写的时候,就经常被它逗笑。”
“笑”是对正常生活的感知,也成为陷于泥淖之中的人们的一根稻草,哪怕它如此轻盈,不堪一握。
 ● 李翊云在新泽西州普林斯顿家中
● 李翊云在新泽西州普林斯顿家中
她曾在与抑郁症交锋期间,读过多位作家的信件、日记、传记和作品,他们有的受困于不幸的家庭关系,有的被恶疾缠身多年,有的背井离乡一生坎坷......“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就像时间流过每一个人,在他们的身上留下沟壑纵横的烙印,这让她愈发清晰地感受到了命运的不可理喻之处,当追问没有必要,当同情变成对普罗大众的悲悯时,她更愿意以实际行动去填充生命的虚无,去超越那些似乎永无止境的痛苦。
儿子离开的那年冬天,她订购了25棵风信子。此前的秋天,她种下了800棵。
“风信子”寓意生命与爱恋,她希望天堂的儿子能收到来自母亲的思念。
2020年,《我该走了吗》出版,这是李翊云首部被译成中文出版的长篇小说,也代表着她愿意进一步拆除心灵的藩篱,去直面那些被割裂与深埋的经历,整饬曾伤痕累累的精神原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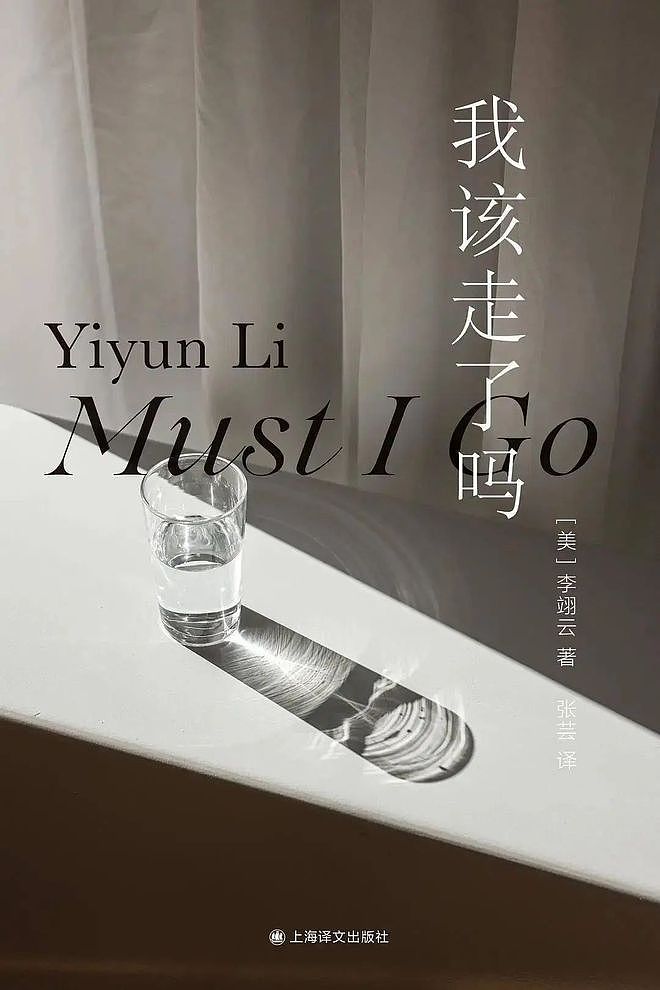 ● 李翊云首部被译成中文的长篇小说《我该走了吗》
● 李翊云首部被译成中文的长篇小说《我该走了吗》
同时,更为了“从我的生命写进你的生命”。众生皆苦,天意无常,所以,她在深味诸般痛楚与心碎后,渴望能从文字的世界里,从无边的幽暗中“升起火光,让从寒冷中赶来的人,可以坐下来烤烤火”。
美国作家西格丽德·努涅斯对这本书的评价展示了她的深刻理解:“《我该走了吗》带我们进入李翊云熟悉而有力的情感领域。它精妙地探索了我们所爱的、失去的和哀悼的将如何塑造、恢复和重塑,让我们成为现在的自己。”
5.无解之谜
在李翊云早期的短篇小说《善良》中,讲述了一个令人心酸的故事,女孩无法接受自己养的小鸡就这么死了。她于是去了厨房,敲开一个鸡蛋,把蛋壳洗净、沥干,然后尝试把死去的小鸡塞进空壳里,想让它重新孵出。
李翊云说,这就是一种绝望的复活,想要试图回到开始,却再也回不去了。
因为她曾经也对儿子如此呼唤:“多希望你还在这里,多希望你还在身边。”
但上穷碧落下黄泉,两处茫茫皆不见。

如今,李翊云的幼子也过早离世,如果代际遗传的不幸成为悲剧的肇始,那么,自我的觉醒与关系的重建是否可以为身处困境的人们指出一条路径?
戛然而止的生命,与未尽的长途,有太多遗憾与难解之谜,它们无法弥补,也难以求证。在《理性终结之处》里,儿子生前留下了一个电子文档,母亲在和丈夫商量后,选择不打开它。“无法知道答案想必最接近人们所说的伤口”。
创伤也许只会被抚慰,从不会消失,但它的存在却是生命无法回避的构成,亦如废墟之于大地,彤云之于天空,亦如爱,之于所有的破碎。
在书的结尾,李翊云以反问的方式表达了对命运的参悟:“深渊是不是可以变成一个人自然栖居的地方?我们是不是可以像接受头发或眼睛的颜色一样,接受痛苦?”
就像当年她种下的那些风信子,长在黑暗的泥土里,却开在每一个春天。文/荠麦青青







 +61
+61 +86
+86 +886
+886 +852
+852 +853
+853 +64
+6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