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民主的失败教训:三大问题需正本清源(组图)
本文转载自hk01,仅代表原出处和原作者观点,仅供参考阅读,不代表本网态度和立场。
上世纪八十年代,面对香港回归这一急迫的问题,邓小平将原本用于解决台湾问题的「一国两制」作用于香港,并承诺「五十年不变」,也因为这一承诺,「五十年之后怎么办」的问题始终萦绕在香港社会,香港的命运探讨也始终围绕2047展开。在香港实践「一国两制」五十年不变的中期时刻,也就是香港回归25周年之际,习近平访港时明确表示,「一国两制」这样的好制度「没有理由改变,必须长期坚持」,自此「五十年之后怎么办」也随之转变为「香港怎么办」。虽然2047大限的梦魇不再,但面对中国之变、世界之变,香港对自身角色和命运的透析,对香港与内地关系尤其是对中国共产党的全面准确认识,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重要和迫切。

香港01:
您在增订出版的著作《香港 文明视野中的新边疆》中提到要把香港从「问题」过渡到「方法」,并指出「如果总结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学习驾驭全球资本主义经济的成功经验,其中最重要的一条就是善用香港的『一国两制』,『在游泳中学习游泳』。」「在『一国两制』下,台港澳地区无疑会成为中国迈向世界舞台的不可或缺的重要阶梯。这就意味着香港在国家战略格局中的重要性,就要从改革开放以来单一的经济战略定位转向双重定位,即不仅要强调其经济战略定位,而且要开启其政治战略和文化战略的新定位。」面对今天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您在书中也提到中国必须承担起全球治理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责任,成为国际秩序的「责任承担者」,「这就意味着中国不仅要具有驾驭全球资本主义经济体系的能力,而且要具有掌握驾驭全球资本主义政治体系的能力,并在此基础上展开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香港过去这么多年的政治化过程,对接下来的双重定位尤其是政治战略新定位意味着什么?香港的政治化尤其是民主选举方面的实践,对中国提升掌握驾驭全球资本主义政治体系的能力方面有什么帮助?您刚提到,未来需要制定新的行政长官普选方案。过去几年采访港澳领域的学者,不少人会对香港错失实现双普选扼腕叹息,毕竟如果8·31方案顺利通过,香港将成为台湾之外中国唯一实现全民普选的地方,而这样的历史拐点也已经一去不复返。

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强世功。(环球时报)
强世功:
对中国来说,香港的竞争性选举可能不是成功经验,某种意义上可能是失败教训,台湾民主化也同样如此。香港的民主选举模式,完全是按照西方的所谓竞争性选举来进行的。而中国这么大的国家,无法采取竞争性民主的思路,所以我们今天讲「中国式现代化」,意思很明确,那就是中国要走符合国情现实和历史文化传统的一条独特的民主发展道路。为此,我们需要在「民主」问题上正本清源。
其一,民主与政治权威的关系问题。政治的核心是什么?为什么我们要民主,或民主的政治目的是什么?政治的核心问题就在于解决政治统治的正当性问题。启蒙哲学摧毁神权政治的正当性,就必须通过民主来奠定政治权威的正当性,这就是人民主权的意涵所在。在这个意义上,确立政治权威是目的,「民主」这个概念的核心是「主」,即主权权威。然而,民主制度推行的过程中,恰恰面临的根本问题就是很容易摧毁政治权威,但很难建立政治权威,法国大革命的历史就是如此,晚清以来中国民主化历程也是如此,今天欧洲、美国的民主选举也面临这类似的问题。
早在《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中,亨廷顿集中反思并批判了美国二战后在第三世界国家中推行民主化运动所带来的权威秩序解体,由此导致了冲突、混乱、屠杀、暴乱、割据、战争以及革命等。基于对这些历史经验的反思,亨廷顿在政治学理论上提出要区分「现代性」(modernity)与「现代化」(modernization):前者乃是在欧洲历史经验中所体现出来的从传统社会转向现代社会之后的一种全新的生活方式,包括市场经济、自由法治、宪政民主等等;后者乃是从传统社会的权威解体到建立新的社会权威的具体历史过程。如果说前者属于规范性分析,那么后者就是政治历史的分析。在这个具体的历史进程中,有的国家成功了,有的国家失败了,即使在现代性的发源地欧洲,英美往往被看作是成功的例子,而法国大革命之后的政治不稳定往往被看作是失败的例子。
正是基于对历史经验的总结,亨廷顿在其著作中集中批判了西方政治理论中将自由民主政体看作是最高政治理想的意识形态教条,从而主张政治的首要问题并非自由民主,而是如何避免陷入「人对人是狼」的无政府状态,这种无政府状态被亨廷顿称之为「政治衰败」。因此,在亨廷顿看来,政治的首要问题不是政体问题,而是权威问题,就是如何建立稳定的政治权威,由此才能奠定政治秩序,避免政治衰败。而这个理论无疑是亨廷顿与福山的「历史终结」理论的根本分歧,后者是一种规范理论,而且将政治的根本问题集中在政体问题上。直到后来,福山才面对现实修正其理论,关注国家能力问题,国家负责任的能力必须建立在权威的基础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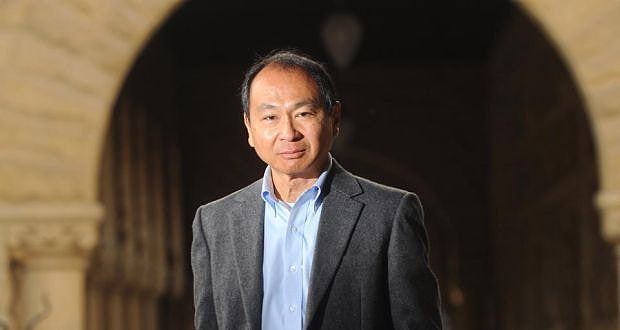
美国政治学者弗朗西斯·福山因提出「历史终结论」而名噪一时。(网络图片)
因此,作为现代化历史进程中的一部分,伴随着市场经济摧毁了传统经济,导致传统社会结构的解体,理性化和自由化的生活方式摧毁了传统的信仰、道德和社会生活规范。然而在传统权威随之解体之后,如果不能有效地建立起民主程序所生产的权威,那政治民主化就会遭遇最大的危险:陷入无政府状态的政治衰败之中。二战后美国在非洲、拉美和东南亚推动的政治民主化普遍遭遇到这种政治衰败。
正是从如何克服政治衰败这个问题入手,亨廷顿考察了不同的历史和文化背景下产生的不同途径。比如土耳其在民主化进程中遭遇到政治衰败,最后是通过建立「军人政府」恢复了政治秩序。而在中国,是通过共产党政府有效地克服了政治民主化带来的几十年的混乱和内战,恢复了政治秩序。正是基于对历史事实的尊重,即使在「冷战」的意识形态背景下,亨廷顿依然高度赞成了苏联和中国通过共产党一党执政来克服政治衰败,实现了有效的政治治理。因此,他认为「第三世界」能够有效实现政治民主化的导师不是在华盛顿,而是在莫斯科和北京。华盛顿的模式带来的是政治衰败,而莫斯科和北京的模式建立的是有效的政治秩序。在总结历史经验的基础上,亨廷顿明确反对意识形态化的激进民主化主张,而主张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有效压制民主意识形态化产生的过高预期,并建立更多能够让公众参与的民主制度渠道,从而巩固并提升民主政治的权威。
其二,区分「选主」与「民主」的问题。在民主问题上,亨廷顿使用的不是「民主」或「竞争性选举」这些概念,更多是「政治参与」这个概念。他将民主理解为「政治参与」问题,因为这种参与不仅有利于形成政治权威(即政府乃是我们的政府),而且有利于政府做出正确的政治决策(参与决策咨询)。如果从这个角度看,港英时期最成功的「行政吸纳政治」就是通过大规模开放「政治参与」而奠定港英殖民政府的权威。如果从这个角度看,投票选举仅仅是民主的一种方式,香港人熟悉的各种形式的公众咨询、政治协商都属于民主政治的一部分,特别是随着行政权力的扩张,全球都出现「审议民主」不断加强的趋势,以至于传统选举的代议民主不断削弱。
如果「民主」的角度看,竞争性选举实际上是「党争」,最后必然堕落为「选主」。这方面西方有大量的学术文献,即老百姓仅仅投票,但无法做「主」,真正做主的乃是大资本集团,尤其是新技术推动的大众媒体,资本控制着舆论,导致竞争性选举堕落为资本的游戏,老百姓被资本控制的舆论所左右。正是在选举的竞争性乃至公众表演性,导致选举政治变成了「为反对而反对」的党争,挑战政府的权威和政府推行政策,最终服务于全球资本的利益。今天欧美的竞争性选举也陷入这个党争怪圈,导致民粹主义政治兴起,出现特朗普式的政治强人。

美国前总统特朗普(Donald Trump)2023年6月13日在贝德明斯特(Bedminster)高尔夫俱乐部发表讲话。(Reuters)
回到香港,我们看这些年的竞争性选举,在「选主」背景下,反对派大佬拥有资源而始终控制着立法会议席,年轻一代无法上位就走向街头政治。区议会选举原本服务地区,可在选举机器的舆论动员和操控下,没有在地区服务过一天的反对派明星人物,可以轻松当选区议员。香港竞争性选举导致的「占中」、「暴乱」的动荡局面难道是香港大多数老百姓所做的「主」吗?显然,在这种竞争性选举机器的操作中,香港的「民」已经无法做「主」。在这种情况下,在民主制度选择上就要遏制资本和媒体对选举的控制,推动「选主」向真正的「民主」转变。
其三,民主发展的社会文化基础问题。托克维尔在比较民主在美国与法国的不同境况时,发现民主稳步发展有赖于三个要素:自然地理、法制和民情(mores),其中法制比自然地理更重要,而民情比法制的贡献更大。如果我们以此作为关照,就会发现香港地处祖国边疆,处于高度自治的状态下,民主选举很容易触发对中央的离心力量,不利于民主的发展,香港内部成熟的法制环境也有利于推动人人平等,然而香港民主面临的最大问题则在于「民情」。
一方面,香港的商业文化中有一种资本崇拜,而在港英殖民统治下又形成一种精英崇拜,无论在政府公务员体系中,还是在大学、公司等社会生活中,等级秩序森严,由此也形成商业世家豪族把持香港的格局。
另一方面,作为中央直辖之下的地方行政区域,香港的民主政治直接影响到如何处理特区与中央的关系问题。在这个问题上,长期殖民统治以及两地文化教育的不同,导致香港人对内地和中央缺乏认同和信任。1989年的天安门风波和此后彭定康的和平演变战略,进一步加深了中央与香港之间的不信任。香港回归之后左派与右派的恶斗,激化了香港历史上的旧怨新仇。香港的和平过渡并没有完成「去殖民化」的政治任务,导致香港居民的国家认同进展缓慢。香港自认为与西方世界连为一体,在「历史终结」的世界帝国时代,被西方看做是对中国进行「和平演变」的基地。近代以来中国与西方的冲突遭遇,使得香港处在比内地更为「现代」、更为「西方」、更为「世界」、从而更为优越的观念体系中。

前港督彭定康。(资料图片)
在这种背景下,香港推进竞争性选举必然引发「两制」之间的分歧,引发后来的「港独」风潮。在这方面,台湾就是前车之鉴,民主化引发「台独」思潮的蔓延。前些年,我在访谈中提到要警惕「香港问题台湾化」就是强调竞争性选举推动分离思潮。中国是一个文明大国,我们的文化传统崇尚和而不同,历史上始终抵触防范「党争」。「党争」将集团利益置于整体利益之上,最终背离政治的公共性,这往往成为王朝衰落时期的景象。中国是多民族、多文化、多宗教的大国,竞争性选举的「党争」必然产生离心力量,导致族群、宗教和文化的纷争。
如果我们从这个三个方面看,中国式现代化所推进的民主必然是基于民本传统的民主,也是群众参与式民主,也是精英阶层为人民服务的民主。
香港01:
所以是不是可以说,虽然双普选的大门还没有彻底关上,但香港在政治上已经丧失了对中国的示范意义?如果这样的话,那「一国两制」这一制度设计长期坚持的支点和基础为何?陈端洪老师在《理解香港政治》一文中认为两制对峙给国家发展注入了新的动力。随着香港内部政治对峙精神结构的弱化(比如立法会成了清一色的建制派),「一国两制」该如何继续为国家发展注入动力?
强世功:
我想先问一个问题:香港人对2047以后香港的想象是什么?不少人的想象是香港要成为一个半独立的政治实体,中央不要管我,可以继续骂共产党,铜锣湾书店可以继续搞事。总而言之,就是香港自己管自己,中央最好是象征,什么都不要管。这样的想象,实际上已经接近一个大国和小国的对等关系。陈老师提出的「对峙」显然不是这个意思。「对峙」的基础是「两制」,然而,「两制」的前提又是「一国」,因此「对峙」的含义不是政治对立、敌对或冲突。过去,香港反对派曾经为究竟被称之为「民主派」还是「反对派」有过争论,有人甚至用英国语境中「女王陛下的反对党」来阐述「反对派」。
从这个角度看,香港反对派应该是「对中央保持政治忠诚的特区反对派」,他们对应的是「对中央保持忠诚的特区建制派」,双方在对中央保持政治忠诚的前提下,基于香港本地不同的利益和文化观念而形成「对峙」或互动。在这种背景下,骂共产党如果是言论自由那当然没有问题,但要是变成为「反共」的政治宣传乃至政治行动的一部分那就不容许,这个问题邓小平当年有明确的论述。

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陈端洪2016年撰文《理解香港政治》,提出对峙结构。(国新办)
因此,「对峙」的前提是维持国家统一和中央政治权威这个前提下的「对峙」,「对峙」不是敌对,而是不同中的「互补」,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和而不同」,在「一国」问题上要「和」,在这个前提下保持「两制」之间的「对峙」,这才是「一国两制」的精髓。由此,立法会中建制派和反对派搞得你死我活、打成一团不是「一国两制」,反对派从根本上不认同中央政治权威、瓦解「一国」基础,那就不是「对峙」,而变成「对立」。同样,立法会中「清一色」显然不符合「一国两制」的精神,在香港不能批评共产党,不能骂共产党,只能唱赞歌,那也不符合「一国两制」,对这个问题邓小平也有明确论述。
从这个角度看,从邓小平时代到习近平新时代,中央的「一国两制」原则以及对香港的政治承诺始终没有变。邓小平当时在驻军问题上说的很清楚,总有一些问题是香港自己解决不了而需要中央出手。今天中央说得也很清楚,在涉及到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涉及香港繁荣稳定的根本问题上,中央非出手不可,这个「出手」也包括经济政策上的支持,比如中央出手帮助特区政府应对亚洲金融危机,中央推动粤港澳大湾区经济发展等。我们都知道,2003年之前,中央都是尽量不干预,但2003年的七一大游行之后,是香港反对派及其背后的政治势力首先打破了「一国两制」的内部平衡,反对派不断否决中央支持的政改方案,甚至发展到「占中」、「暴乱」和「港独」,这才迫使中央不得不出手来正本清源。
因此,不能说中央对香港的政策改变了,「一国两制」的承诺始终没有变,中央对保持香港繁荣稳定的总目标也没有变。在「大局已定」的前提下,香港人反而需要打开一个心结,那就是在香港六七暴动以后,在「一国」的大前提下怎么对待中国共产党的问题。这是所有问题的核心。如果不认同中国共产党在中国包括香港的政治权威,那么中央今天所做的一切都会被看作是背离了「一国两制」,因为他们脑子里的「一国两制」乃是香港作为独立或半独立实体的想象,这显然不符合「一国两制」的初衷和现实。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领导者,是中国文化传统的继承者和发扬者,是中国现代文明的推动者,是「一国两制」方针的创立者,也是「一国两制」事业的领航者,不理解中国共产党和近代中国革命,怎么能够全面准确理解「一国两制」?
本文转载自hk01,仅代表原出处和原作者观点,仅供参考阅读,不代表本网态度和立场。







 +61
+61 +86
+86 +886
+886 +852
+852 +853
+853 +64
+6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