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年前的海淀黄庄, 第一代被“鸡”大的娃, 后来怎样了?(组图)
本文的主人公刘晓寺,便是最早在海淀黄庄长大的那批孩子之一。从他五岁起,人生便要面对无数的考试、面试与比较,才能顺利进入下个阶段。

奥数班的教室被一分为三,讲台上的老师,高出课桌一头的小学生,和强打着精神记笔记的家长们。鸡兔同笼、火车追及、水池注水,亘古不变的数学难题构成了一代人的共同回忆。
而奥数班只是其中一环,灌满孩子们的童年的,还有少儿英语、演讲比赛、满分作文培训班。
在北京海淀黄庄,培训机构分布在写字楼的各个角落,刚需的,冷门的,合规的,偷摸摸的。被迫浸泡其中的孩子们,用今天更潮流的说法,叫做鸡娃。
本文的主人公刘晓寺,便是最早在海淀黄庄长大的那批孩子之一。从他五岁起,人生便要面对无数的考试、面试与比较,才能顺利进入下个阶段。
今年他23岁,当他回望过往的成长经历,海淀黄庄的教育神话,别人家的孩子,没有尽头的卷子和补习班。那些有形或无形的比较,似乎仍旧在长久的时间里围绕着他,而他从未走远。
以下是他的讲述。

天之骄子
2004年,五岁的我牵着妈妈的手,跟着她去找老师。小学位于海淀区中关村的核心区,寸土寸金,兵家必争。因此教学楼的走廊也出奇窄小,教师办公室门口的走廊更是常年不见天日。只有头顶微弱的白光,隐隐照亮前面的路。走廊尽头的门开了,老师推门而出,我在妈妈的指引下远远地和老师打招呼:“老师好!”
“不许拉着妈妈的手!”
五岁的我,从来没听过这样的指令,因此惊慌。妈妈倒是听话,迅速把手抽了出去。
于是,失去了手的我,如同断了奶的婴儿,站在楼廊里哇哇地哭,更严厉的训斥从走廊的另一侧呼啸而来。我已忘了这一天如何收场,但我会记得,作为中关村某小的一年级学生,我不再享有抓着妈妈的手的权利,当然,更不享有哭泣的权利。
这就是我的“开学第一课”。
进入这个学校,并不容易。印象里还需要一个象征性的笔试。一群几十公分高的小生物,还没有上学,就已经上了考场。老师在前面坐着,每个人做二十道数学口算题,大概是加减法或比大小。然后上交,老师现场判卷,得胜者就可以拿着一张二十分的试卷,出校门,换取今天的冰棍。
没人知道,为什么还没有上过学的孩子,应该会这些题目。但一批孩子,已经因此被拒之门外。

几乎所有北京人都知道这所学校的名字——在2021年的毕业典礼上,郎平、康辉、莫言、雷军先后为这些,也许对他们的成就毫无概念的小学生们寄语。
同样的,在我还在读小学的时候,隔壁班的同学曾在祖国60周年庆典的花车上对着胡锦涛主席微笑;学校的管乐团、合唱团也曾在维也纳的金色大厅演出。
我三年级的时候,学校举办了一场少数民族手拉手的活动,邀请少数民族的学生进京——所有路费由对接的班级自筹。于是,全校的小朋友们集体行动:卖废品,爱心义卖——这当然凑不齐一趟往返的飞机票。因此,学校又举办了“爱心捐款”,只要父母献出一点爱,小朋友的梦想就可以因此实现。
家长们献了爱心,小朋友们达成了愿望,学校的宣传语当然是——某小的孩子自筹路费,送小伙伴进京——于是所有人都为小朋友的机智喝彩。
当时,我们班“牵手”的民族是德昂族。大概是在同学家长的帮助下,我们真的联系到了一位云南山区的德昂族女孩——曹春香——我现在还记得她的名字。我们筹集了她来北京的一切费用,带她逛北京,看升旗,吃烤鸭,甚至还去了北京大学。
在北大的未名湖畔,四个北京人和一个云南人,共同许愿要在北大相见,小小的眼睛闪着比未名湖水还清澈真诚的光——毕竟,我们可是这所小学的天之骄子。
当然,我们最后也没能相见。

初代鸡娃
我总是和朋友吹嘘,我小学做的试卷比很多人中考做的还要多。毕竟,我们可是“鸡娃”的老祖宗。
学校没有期中考试,但一学期有两次验收,外加期末考试。一个学期被分为三段——不是在准备验收,就是在准备期末考试。
数学的口算验收是我的噩梦。在模拟验收时,我五分钟只能做40道口算题,离60道的规定数目相去甚远。
老师一个电话打给了家长——“别人家的孩子都能做完60道,怎么就你们家的孩子就只能做40道!不合格!”
聪明的老师,巧妙地隐去了“别人家孩子”的数量——50人的班上,可能只有五个人可以达成这个目标。
但家长不知道有多少人可以做出来,家长只知道,自己的孩子不能被落下。于是心急如焚,揪着我挑灯夜战。抓来计时器,设定五分钟。
11点的夜晚,计时器唰唰地转动,身高刚过一米的我趴在窗前高高的桌子上奋笔疾书,一边写一边祈祷着叮铃铃的声音慢点响起。
但那声音总归会来,一次次艰苦努力宣告失败,准备迎接从背后袭来的毒打——我后来想,这有没有可能是他们为了泄愤?
一顿并不严厉的打骂后,我擦干眼泪,把计时器又拧到五分钟——偷偷多拧一小个刻度,为自己争取十秒钟的喘息,而后继续奋笔,继续失败,被责骂,而后一切继续。
就在这样的苦战后,我终于在两天的时间内速成为计算高手,验收时,60道题顺利完成。老师家长一片欢呼。第二年难度加大,这样的痛苦又如数重演。

而很快我就知道,验收并不是最大的苦难。
平静是被我姑姑打破的。那天的闲谈里,她偶然询问我的母亲,我有没有什么课外班,母亲细数了我的围棋课,书法课。
“没有奥数课?”我的姑姑惊讶万分。
奥数——这个所有海淀黄庄人的梦魇,在这一刻出现在了我的生活中。但我和我的妈妈知道得已经太晚了。我三年级的弟弟已经学了两年。
于是,在一个热气腾腾的午后,我被塞进了一间装了40人的教室,老师是姑姑推荐的。据说这个机构和某重点中学有合作,如果表现优秀,就可以获得入学名额。
但我当时最感兴趣的,是教材的前几页,印着机构的老师介绍。我在老师的简历中一次次看到了“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的字样,也有些是我那时根本瞧不上的学校,比如“中国人民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一节课下来,走在楼道里,我已经可以清晰认出走廊里路过的每一位老师,并叫出他们母校的名字。
而后,我发现我并不孤独。在这个全北京最知名的奥数培训学校的教室里,几乎没有几个人可以听懂老师上课的内容。
当然,他们也不一定会关注那些老师的简介,他们也许会在课上看书,作画,练书法,画素描——这是全北京小艺术家们的殿堂。
但是,这节课上,也一定有那么一两个讨厌的小孩子,不但可以听懂,还可以上台演示,还可以期末考满分,并在家长会上和自己的家长一起收获所有人艳羡的目光。
于是,我们这些小艺术家们,为了成为这些大数学家,在一个个午后走进这间海淀黄庄的教室。

可是到了后面,家长们发现了我们想在奥数课上成为艺术家的梦想,并决定采取行动。某个周末,就像商量好一样,教室的过道里突然间坐满了家长。每一个学生身边,几乎都坐着一位家长,所有人坐得比学生还要笔直,聆听老师在上面口若悬河的教诲。
前半节课,家长们认真地摘抄着老师的板书,准备回家给自己的孩子们辅导。后半节课,家长们逐渐败下阵来。我印象很深,我妈妈去听我的第一节课,是我提醒她——“妈妈,醒醒,下课了”。后来,家长们越来越少,但我的妈妈一直坚持在一线,成为了教室里的“钉子户”。
可是,我的妈妈最终也无法听懂。在一个深夜,我们面对着一道数学题束手无策时,拨通了我远在美国的表姨的电话——她本科毕业于北大数学系,硕士毕业于MIT数学系,留在美国工作。半小时后,表姨也在一道火柴棍问题上败北。印象里,这道题老师只用了五分钟就讲完了——这是一道“送分题”。
但天无绝人之路。我们很快发现,高手就在我身边——小我一岁的表弟,我姑姑的孩子,成为了我的数学老师。那道火柴棍的题目,他十分钟就做出来了。我们上同一个小学,他也是学校里有名的数学天才。
后来,我每周末都在我们学校知名数学天才的家里小住。那时我才意识到,天才出自勤奋的真谛。
在我的印象中,三年级的表弟几乎没有在两点以前爬上过床。每天十二点多,我已经困到不行,我的姑姑就放我一马,让我去里屋休息。而我的姑姑,和我的姑父,还陪着我表弟在客厅挑灯夜战。
而且,我周末来我姑姑家的唯一目的,就是学奥数。但我的表弟却不然——练小提琴,学英语,写作文,十全大补。但是,除了奥数,我的表弟显然并不精于其他,于是打骂的家法又一次派上用场。
时常,我躺在房间床上,可以听到我的姑父挥动皮带追着我表弟打的声音,然后传来我表弟的哭嚎,逃跑和我姑父追赶的声音,以及我姑姑在旁边的加油助威——“打他!作文写这么慢!该打!”。于是传来我表弟更大的哭嚎声,和桌椅碰倒的稀里哗啦的声音。
但是,这样的责打并非全无好处。我的表弟在全校的成绩一直名列前茅,并因为奥数成绩优秀而被北大附中录取——那是一所以素质教育闻名的学校。
但他们家后来举家移民加拿大,似乎上北大附中还是普通学校,也并不是非常重要了。

升学之路
至于我的升学之路,则要坎坷地多。
当时,每个重点中学都开设了“坑班”——如果你想来这所学校读初中,就要报名这所坑班,占着这个坑位。我报的某西城区初中,周末的坑班有18个班级,可是,只有前三个班,才有机会进入这所学校,而其他的人,每周末只是来这里陪跑。
当然,前三个班的名额并不固定,这个坑班每半学期一考,考试以后,班级调整,风水轮流转。因此,理论上人人都有机会。
坑班的价格记不清了,可能一万块一学期。我当时报了四个,因此周末的四个上下午,被四个坑班精准划分。老师们讲授的内容不重要——甚至有两个坑班,因为用的是同一套教材,讲授的内容一摸一样。
但这并无大碍,因为所有人看重的并不是教学,而是“机会”和“位置”。我在四个坑班,花着毫无概念的四万块钱,在课上心无旁骛地练习我的绘画技巧,并且在考试时,希望我能进入前三个班。尽管从未成功。

因为坑班盛行,升学压力巨大,学校的课业难度也陡然提升。除了语文课,我们几乎每节课都开始用“自编教材”,试题的构成基本是一些重点中学升学题。
而那些升学题,很多都是中考,甚至高考的原题——在小学五年级时,我第一次接触了高考英语的“完形填空”。
没有人会问你是不是听懂,是不是认识那些单词。因为班上总有那么两三个会做的。于是我们拿到试卷,交了白卷,便理所当然地等待着老师表扬那些满分或者接近满分的学生。
再之后,也是理所当然的,既然有同学可以成为满分,那么没有成为满分的同学,也要“努力”成为满分。
自然,音体美改成语数英,科学老师永远请假,自然老师一直缺席。再之后,主科老师可以公然宣称,只有改完错题的同学,才可以去上体育课——这成为某种特权和荣誉。
浑浑噩噩,我等到了毕业。四个坑班,没有一个坑班是成功的。
最后,我凭借跆拳道特长,进入了重点中学。这没什么可丢人的,我们班,只有八个人是因为考试进来的,剩下的都是特长生,推优,或者随机分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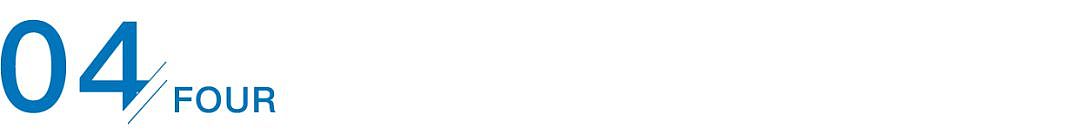
走不出的海淀黄庄
可是,海淀黄庄,别人家的孩子,却似乎成为了我头上永恒的诅咒——别人家孩子能做到的,你也能做到。有形或无形的比较,时刻成为我噩梦的源泉,被抛下被淘汰的压力,则成为我失败后继续努力,而后继续失败,继续努力的唯一动力。
初三毕业时,我保送了自己学校的高中。可是高中第一天,老师却在班里说——“你们有没有思考过,为什么自己考不上人大附中?”——人大附中,别人家的学校。
高三毕业的时候,我考上一所外地的985大学。在亲戚朋友的聚会上,大家听说我学校的名字后,总会问——“为什么不留在北京呢?”
后来出国读书,上了一所常春藤学校,但并不是哈佛耶鲁。于是,那些质疑再一次理所当然地纷至沓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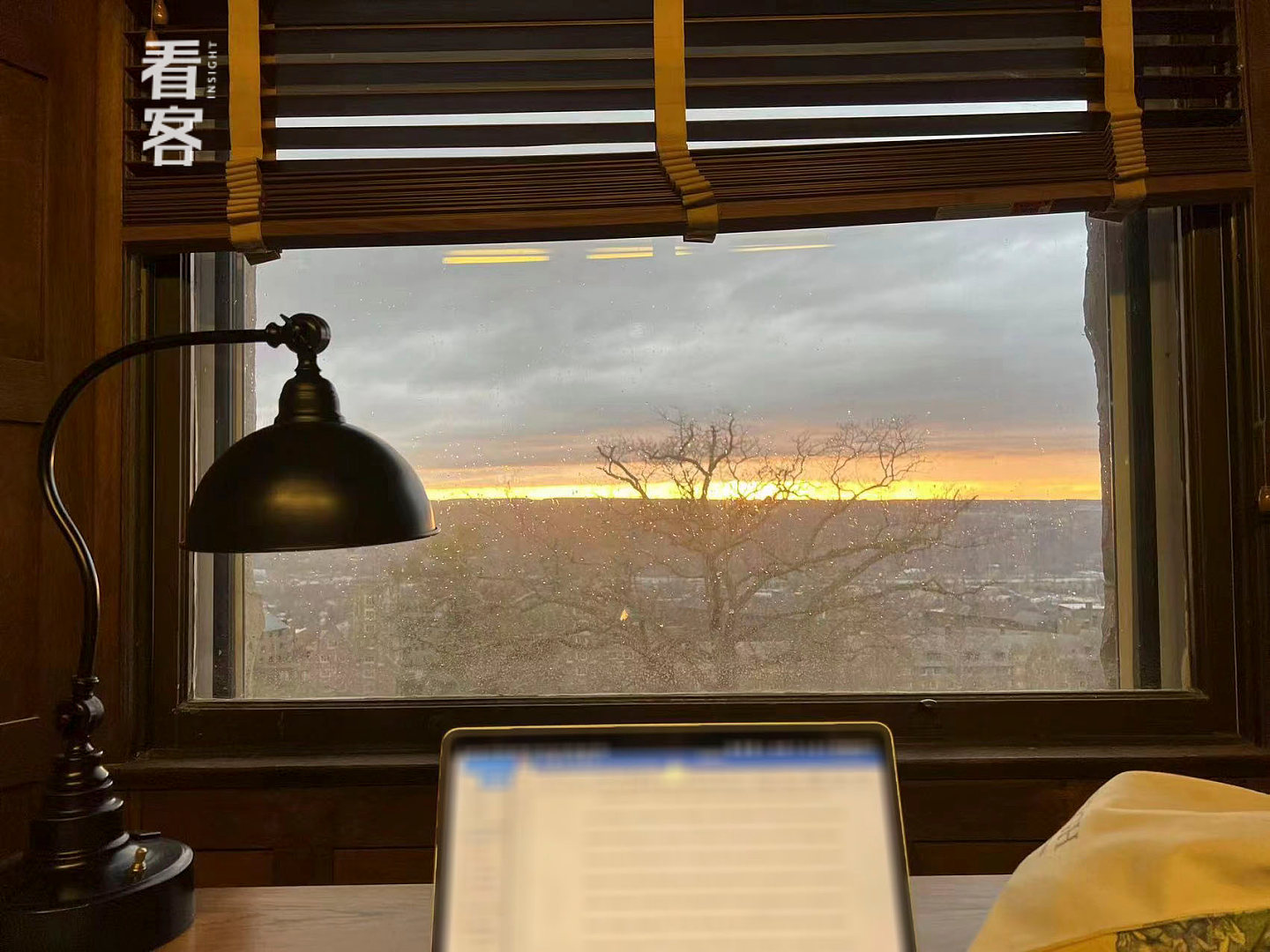
我读研究生时,学校窗外的风景
无论中考,高考,还是出国,我都拼尽全力。可是我终于还是无法成为那个别人家的孩子。
于是在某一刻,回望过去,却发现自己始终在为另一座山而奔跑,跑上了一座山,看另一座山更高,于是继续奔跑。没有人保证另一座山头可以许诺你快乐和幸福。甚至,我可能就在别人正在仰望的那座山头,可这样的安慰无济于事,因为你知道,远方有更高的山。
于是你必须奔跑,成为那座山的阴影,几乎是你的宿命。
我当然很理解我的父母。如果你不成为山尖上的人,就只好成为山脚下的芸芸众生。
而当你跟他们抱怨所有的不快乐的时候,他们只会说,别着急,那是因为你还没有到山顶——可其实连他们自己,都未曾见过山顶的模样。
我们,就活在山尖的神话里。
前些日子和朋友打电话大哭,说感觉未来无望。现在想想,无望的理由也很好笑——作为一个北京人,竟然在北京没有自己的房子。于是想见自己未来在就业市场、婚姻市场可能遇到的种种不如意。朋友安慰我——很多人都在北京没有房呀。我反驳——可是有人有房子啊。
在那一刻,我又想到了海淀黄庄的古老神话。哪怕有房子的人是少数中的少数,哪怕做对奥数题的概率是百分之一,我们其他的百分之九十九也要为此而努力。
因为赛道是如此的单一,标准是如此的恒定,成王败寇的思路是如此深入人心。而在神话下的我们,毫无喘息之机,必须创造着一个又一个“神话”,或成为“神话”话语中的众生。
也许,至少,我们曾经参与了某一个神话的书写——海淀黄庄的“教育神话”。







 +61
+61 +86
+86 +886
+886 +852
+852 +853
+853 +64
+6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