凌晨12点,我在上海街头捡垃圾,想象不到的快乐 (视频/组图)
一线城市的年轻人,
找到了新的疗愈方式:捡垃圾。
把马路边的家具、物品,捡回家用。
一把椅子、一个沙发、甚至一扇门框,
经过清洁和再改造后,重新有了新家。
这样的生活方式,还有一个专属英文词“stooping”,
意为“把废弃物品捡回来循环使用”。

 上海stooper黛西捡到的沙发
上海stooper黛西捡到的沙发
这些“垃圾猎人”们,不少是95后,
面对大环境和个体生活的不确定,
在大城市打拼的年轻人,
选择能不花的钱不花;
同时,他们也不想放弃生活品质,
以自己的审美,动手去改造。
用捡代替买,有人说省了大几千;
有人认为垃圾捡得好,
需要拥有发现和再设计的能力,
有人甚至用捡来的“垃圾”拼装了一个小花园。
一条与几位stooper聊了聊他们的捡宝故事。
95后年轻人,捡垃圾成风


上:街头被丢弃的尚好的家具,在物质丰富的今天并不少见;下左:武楷斯,95后,从大学念书期间就爱上了旧物,他自称是个“收破烂”的;下右:国庆节后收到的老式冷暖风机
广州的武楷斯,兴奋地发来他从凌晨5点忙到中午的战利品,其中有一台嫩绿的冷暖风机,是30多年前生产的。作为一个职业垃圾猎人,95后的他收破烂、卖二手已有7年,今年9月,他开设了“stooping广州”,提供捡垃圾的资讯,刚刚起步的账号略显冷清,他说自己每天都在羡慕北京stooping人群的火热。
他说的这股热潮,最初便是从今年6月的上海吹起,延至北京、杭州,如今来到他希望可以带动的广深地区。

96年温州姑娘波妞,工作生活在上海,第一个把stooping、stooper概念引入国内
6月的上海,结束了2个多月的大规模居家隔离,温州女孩波妞恢复了她例行的夜间捡垃圾,捡宝的范围,是她家所在市中心的梧桐区。
边荡马路、边捡垃圾,是96年的波妞独特的治愈方式。她从伦敦大学学院研究生毕业,来上海工作已有2年,负责一所国外大学在国内的市场工作,招生季经常加班到晚上11、12点,开学后就是淡季。

波妞会把自己看到的宝,打上标签
即便加班到深夜,从办公室步行回家的十几分钟,是她在一天紧张的格子间生活后,独属于自己的时间,她曾经在路边捡到过置物篮、整箱的餐盘,还把一个老式挂衣架带回家。
在路边,波妞看到更多的,是被人悄悄扔出的沙发、桌椅、浴缸、床垫、甚至退役电瓶车。马路上的物品实在太多,她决定分享这些信息,给其他有需要的人。
检查物品、拍照,标明物品状态和地址,发在自己的社交账号,如果有人正好需要,可以根据地址尽快认领回家。波妞会提醒大家,垃圾不能过夜,如果当晚没被取走,隔天会被市容作业车收走。

法国梧桐树下会“长”出家具
起初这些发布引来了意外的指责和质疑,因为账号简介内的英国留学经验,有人说她是富二代来作秀、博取眼球、行为艺术,垃圾就是她自己扔的,真要上班的打工人,哪里有时间和精力来看垃圾。
波妞忍不住反驳:“其实年轻人的时间真的那么值钱吗?看剧、刷手机、买买买,也都是年轻人,我用捡垃圾打发时间,其实没什么差别。”


stoopingnyc发布的街头家具
发布信息时,她加了几个标签,其中一个是“stooping”,直译是“弯腰”,也可以理解为“弯下身子捡东西”。后来渐渐引申为“把废弃物品捡回来循环使用”。
捡垃圾,但不作为营生手段,中文尚没有恰切的翻译可以对应。正如武楷斯所言,国内缺乏多层次、体系化的“垃圾教育”,在国外,周末旧货市场、出售二手免税、满街的慈善商店和二手店,thrift shop、vintage shop和antique shop,定义明确、分类严谨。“走过经济高速增长的四十多年,刚刚迎来垃圾分类不久的我们,尚处在起步阶段。”

纽约街头的各色“垃圾”,图源:stoopingnyc
波妞的观察和体会深刻,早在伦敦求学期间,买二手物品、逛跳蚤市场就是波妞的日常,有一天放学路上,她发现一对老年夫妇在路边放了四把闲置的椅子,旁边地上写着“free to good house”。她也是stoopingnyc的粉丝,这个社交账号专注分享纽约街头的各种垃圾,为有需求的人提供物品信息,始创于2019年,如今拥有40万粉丝。
她关注的一个法国博主可以捡面包为生,面包房会将打烊后卖不掉的面包,包装好放进专门的湿垃圾桶,这样的食物依然可被食用,“我们这里,湿垃圾真的就是湿垃圾。”
发完信息,波妞搜索了一下stooping词条下的其他内容,没有别的,她突然意识到,自己是第一个把stooping引进中文世界的人。
与城市的另一面相遇
 依靠捡来的宝,波妞和室友拥有了户外小花园,地垫是由捡来的床板改造而成,床板的搬运破费周折,也让波妞感受到了上海温暖可爱的一面
依靠捡来的宝,波妞和室友拥有了户外小花园,地垫是由捡来的床板改造而成,床板的搬运破费周折,也让波妞感受到了上海温暖可爱的一面
相对于一言不合就买,捡,是波妞和身边的朋友甚至邻居的日常。居家隔离两月多后,室友心心念念要搭个小花园,两个女孩用捡来的户外桌、椅,在小区绿地拼凑了一个简易版花园,最后就差一个地垫。
她在一次捡宝时,发现了她们找寻已久的地垫,但木质地垫太重,一个骑单车路过的上海叔叔非常尽心地提供了帮助,这是波妞捡宝中印象深刻的一次,在热心爷叔身上,她感受到了上海温暖、美好的一面。

经过波妞的刷洗,椅子“活”过来了
随着越来越多的人提供线报、转让闲置,波妞建了群,将扔和捡的行为转移到了线上,扔的人发布闲置物品信息,最先认领的人上门自取。至今,波妞的某社交账号拥有了2万多的粉丝、3000多的社区群友。

武楷斯发布的广州街头的宝,独具城市特色
让武楷斯羡慕不已的北京stooping有1.3万粉丝,尽管广州stooping在国庆最后3天迎来了一波涨粉,从300人变成3000人。他无不落寞地说,“感觉这股风是属于北上的,广深还在艰难发育。”
如果不是stooping,波妞、黛西和观观可能不会认识,尽管她们住得很近。通过物品传递的善意和价值观,让这些年轻人在大都市中有了新的连接点。


上:黛西“扔”掉的部分闲置物品;下:黛西捡到的宝
在知道stooping这个词之前,山东女孩黛西已经在上海生活了8年,她很早就在小区的楼道里放一个纸箱,放进自己闲置又卖不上价钱的东西,供大家免费自取。她不是断舍离的拥趸者,“只是觉得扔掉可惜,但又不想囤积。”
关注stooping后,她在线上“扔”了几次东西,捡到的人,去她位于宛平路的家自取,黛西由此认识了几个朋友,包括99年的北京女孩观观。


上:99年的观观;下:观观在遛狗时发现的沙发
观观最辉煌的战绩,是贡献了一次咖啡店的快闪。有天散步,她发现附近一家咖啡店倒闭了,工人正要逐一砸掉店内物品,跟工人师傅确认信息后,观观给波妞投了稿。波妞立马召集了一次快闪,很快,30多个人按地址来到咖啡店,拿走了剩下的东西。
波妞意识到,疫情影响下的店铺变动、人的来去,多少带动了被扔垃圾的质量,她印象深刻的几次高质量捡宝多数便是如此。
2020年的春节过后,波妞通过弄堂阿姨的线报,得知同小区有个外国租客回不来了,要低价处理自己的物品,她找上门,用500块拿走了那位租客的大部分物品。

巨鹿路的西餐厅结束营业,把物品放到路边供人免费自取,图源:又喜商店
7月,一家在波妞家附近开了十年的酒吧倒闭,整店的家具、餐具堆在路边,附近的居民们纷纷闻风而动,“这个好,你拿走。”得知波妞在找水杯,一位阿姨大方地让给她一堆玻璃杯。

捡宝中的观观
马路上还藏着另一重要的城市信息,遛狗的观观在一个月之内遇到过9个床垫。沙发、床垫多了,意味着租客的流动。离开,或者换房子,很多人因为疫情在家待很久,意识到家的重要性,决定换更好的。
波妞的堂哥可能有更直观的体会,他一直在市中心当二房东,作民宿和长租,疫情期间游客减少,租客离开上海,支付能力和意愿降低,堂哥的生意停摆,把出租屋的软装搬回家后,自己也成为离开者,去了三亚。
混迹于弄堂两年,波妞见证了大城市的另一面,八卦、市井、温情、仗义,现在她的普通话夹杂了上海方言,如荡马路、爷叔,她还习得了弄堂智慧,比如收集塑料瓶、纸头,周日一起去弄堂口卖,每次1-2块,如今存钱罐里目测已有20多块钱。

观观家的沙发,是遛狗时在路边发现并捡回来的
如今,黛西晚饭后的散步会带着尺子,以评判街头物品是不是适配家中空间的需求。她有一个好朋友,偶尔加入她的捡宝行动,捡到好东西时开心,一无所获时互相安慰。
她们的捡宝好友观观,则是在自己日常遛狗时,顺带stooping:出门看垃圾、捡垃圾,自己不要的、尚可用的物品,拍照发群、投稿。
从上海开始,stooping扩散到了广州、北京。北京的二狗,受到波妞的启发,建立了“Stooping北京”,如今已有1.3万粉丝。二狗之前在互联网教育行业做产品经理,七月份被裁员,没有找到工作,想给自己找点事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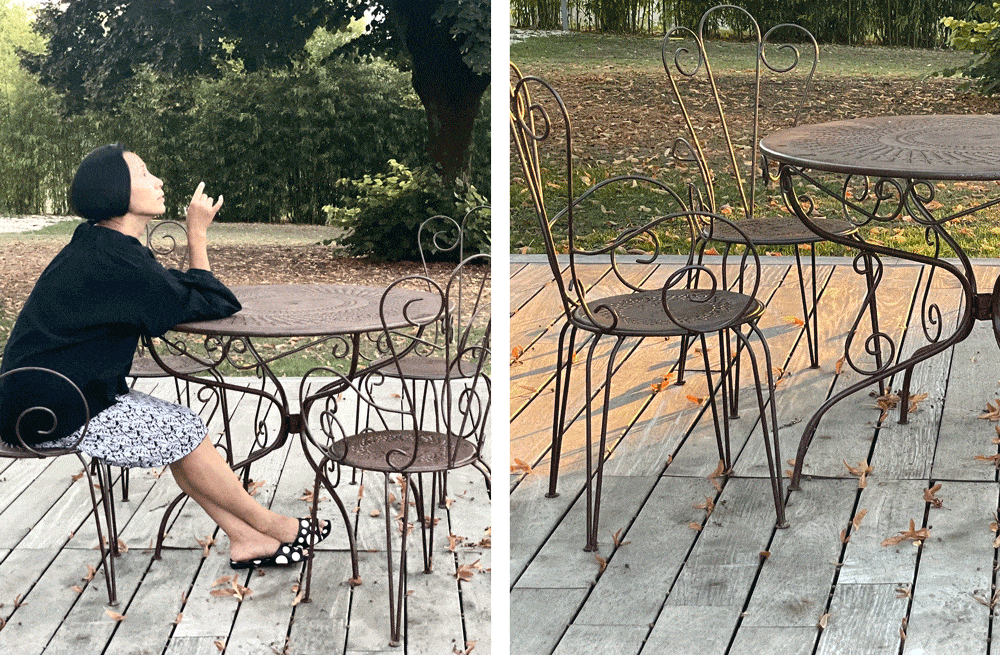
磨掉铁锈,重新上漆,桌椅得以继续使用
8月,知名设计师蒋琼耳,也参与了一把stooping,她将一套被扔在街边的生锈桌椅捡回家,重新打磨、上漆,桌椅得以继续使用。

武楷斯说家里面的床垫、衣服、鞋子,袜子,都是捡来的
“Stooping广州”的建立者武楷斯则是旧物圈的名人,他在大学求学期间就爱上了收垃圾,花钱收来的破烂堆满宿舍,引来宿舍管理员出手,他只好在校外租了间房堆放破烂,房租每个月1000多块,比他买的“破烂”都贵。毕业一年多后,武楷斯在广州成立了自己的旧物商店。
stooping兴起以后,他建了“Stooping广州”,捡垃圾7年,他见到大城市的另外一面,一个活跃在深夜和暗处的、不那么光鲜的平行宇宙,由海量的垃圾构成,他希望借此让人重新审视垃圾,不是简单的一扔了之。
捡垃圾的年轻人们怎么了?关于低物欲、可持续和再创造

留学期间的波妞
波妞回国后,执意留在上海,不接受父母让她回老家考公务员、结婚的建议,只是遵守着双方约定的底线,不在朋友圈发“垃圾”,否则“嫁不出去”。
面对大环境和个体生活的不确定,来一线城市打拼的年轻人,选择更为扎实和接地气的消费方式:能不花的钱不花。
另一端,是成长中接受的生活美学和垃圾教育,让他们可以不放弃生活品质。波妞悉心搭建了小花园,用捡来的餐具好好吃饭,“既接地气又接洋气”,她这样总结自己的生活方式。
相比于透支消费的“精致穷”,stooper们践行着另一种“精致穷”:理性消费,但不减对生活的热爱。想要的东西,不是超前消费,而是自己动手去创造,不被自己卡上的余额限制。

不再被主人需要的的物品,路人多半也对它们视而不见
由于可捡的东西太多,波妞不得不对垃圾断舍离。“捡到的宝,远比你想象多。”决定捡的那瞬间,心中已有大致的规划,包括后续的改造和再利用,不是无脑囤积,而是有计划和更有主动性的选择。
波妞对自己的生活和物品关系,亦有着清晰的判断。“作为租房党,我希望有一天我要搬家的时候,可以背个包就走,把屋子里的东西都留给下位租客,因为我没花什么钱买这些东西。我可以随时重来,用新的物品打造新的家。”
对stooper们来说,捡垃圾除了要冲破既定偏见,也暗含了审美能力,还有一定的动手能力。东西脏了可以清洁、消毒,也可以被二次开发出新功能。

黛西的闲置,已去了新家
stooping圈子普遍的共识是,一个人的垃圾,是另外一个人的宝藏。在stooper眼中,判定垃圾的决定性瞬间,不是被原主人扔出家门、满身脏污立在马路边,而是被扭得缺胳膊断腿装进清运车。

求学期间的波妞,全身上下几乎找不到logo
波妞早早放弃了以某某品牌作为自己的身份标签,转而更关注物品本身的功用和美观。在伦敦求学期间,她所在的留学生圈子里,一直盛行着隐形的“全身大牌贴标签比赛”,波妞说自己从小耳闻目睹,知道父母挣钱不易,真的买不下手。
观观则是在毕业后,一度迷失在买买买的短暂快乐中,眼见家中堆积愈多,她开始读《极简生活》《断舍离》,喜欢上极简生活,也是因为关注类似的生活方式博主,她刷到了波妞。

黛西的自由职业生涯起步于疫情
黛西是85后,2年前开始自由职业,从前是4A广告公司的文案,由于经济下行,广告行业近年来倾向于雇佣短期项目参与者,而不是雇佣长期人员,以减少成本,“经济形势不好,反而成就了我能自由工作。”在黛西看来,“捡垃圾是唯一一种不劳而获的方式,甚至能捡到很好的东西。”

波妞在居家隔离结束后,开始尝试种植,种薄荷的盆器是一个洗拖把的池子
波妞尝试向零垃圾排放看齐,在居家隔离之后,她尝试在家用波卡西堆肥法处理湿垃圾,最终还是被异味打败了。波妞回到stooping,延续物品的生命,一种入门级的、人人都可参与的环保生活方式,不但不费钱,还省钱。

参加海滩捡垃圾公益活动的观观
观观在接受采访的9月底,参加了一个金山海滩的捡海洋垃圾的活动,她兴奋地分享着结束捡垃圾后,她带着大家一起做冥想、放松:“真的很开心。”
在充满不确定性的世界,选择蛰伏、趋于保守,转入低能耗运营的同时,依然不忘悉心经营自己的一方天地,热爱生活和世界。
这些“捡垃圾”的年轻人们,也许昭示着生活的另一种可能。







 +61
+61 +86
+86 +886
+886 +852
+852 +853
+853 +64
+6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