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怕被与世隔绝” 澳洲驻华记者撤离,发文讲述亲身经历(组图)
本文译自AFR、环球网、ABC,仅代表原出处和原作者观点,仅供参考阅读,不代表本网态度和立场。
出于对两名记者在华安全的严重担忧,本周一,澳大利亚驻华使馆及两家澳媒体机构已安排两名澳籍记者离开中国,他们分别是ABC的Bill Birtles和AFR的Michael Smith。
据了解,这两名记者受到了中方有关部门的询问,9月8日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在主持例行记者会时回应该事宜,表示“中方有关部门在办理一起案件的过程中,依法对两名澳大利亚记者开展调查询问工作。此举属正常执法行为。”
9月9日,记者Smith在AFR发表文章讲述了自己接受调查及离开中国的经历。
以下为全文翻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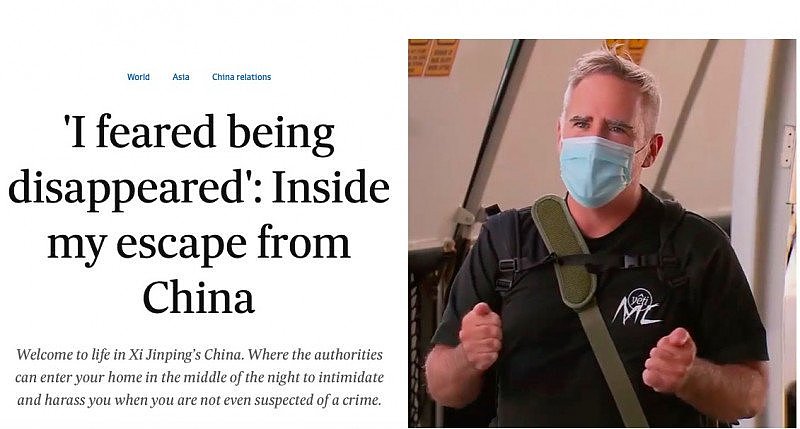
午夜刚过,中国情报、安全和秘密警察机构的人来敲我的门,沉重的敲门声让我从梦中惊醒,我急忙跑下楼,以为是朋友或邻居遇到了麻烦。
相反,敲门的是来自国家安全部的6名身着制服的警察和一名翻译,前者向我出示了身份证明,问了我的名字并要求进门,于是我便将他们领进客厅。
我当时穿着短裤坐在沙发上,周围都是不速之客。一名警察用一台大摄像机拍我,好像这里变成了演播室,一束聚光灯照进了我的眼睛。
他们用中文读了一份声明,不过我无法看清三页纸声明中的每一个字(已被机翻成英文),但大致意思是,我是一个案件的利害关系人,在回答与调查相关的问题前,无法离开中国。
这次午夜拜访过后,是过山车的4天。因澳籍记者成蕾在北京拘留,在收到外交经贸部的建议后,我立即决定离开中国,行李也已打包好,准备第二天晚上就搭乘飞机前往悉尼
事实证明,澳洲政府的建议是正确的。当这名警察宣读一份概述中国国家安全法的文件时,我在想,我是否也会像成蕾一样,在中国“臭名昭著”的监狱中“与世隔绝”。
10分钟后,警察问我的电话号码是多少,让我在他们刚刚宣读的声明上签字,并按指纹,之后他们便转身离开。
我松了一口气,在知道我不会被拘留后,便跟着他们到外面想问个明白——刚才到底发生了什么?他们想要什么?能否给我一份文件的复印件?我的要求被粗暴地拒绝了,他们在夜色中走了,我的邻居在外面看着这一切,看起来很害怕。

Michael Smith和狗狗Huge在他上海的住所外(图片来源:AFR)
这一切就像间谍电影中的场景
欢迎来到中国生活,在那里,当局可以半夜进入你家,在你甚至没有犯罪嫌疑的情况下,让你认罪,还要在被拘留6个月甚至更久后才能见到律师。
这起事件有两个惊人之处:一是虽然外国记者经常被驱逐出中国,但这是他们第一次被禁止出境。其次是身处北京的ABC记者Bill Birtles也身陷类似事件——7名警察上门问询。
我们是当时澳洲仅剩的两名驻华记者,此举显然具有政治性,我们也都得到了澳大利亚驻华使馆的通知,那一晚,我难以入睡。
第二天早上,我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走进上海领事馆的办公室,那里距离我家只有5分钟的车程。而Bill也联系了澳大利亚驻华大使馆。
在经过一系列沟通后,大家一致认为我们需要领事保护。之后我坐着领事馆的车回了家,车上挂着黑色车牌,如果中国的安全官员想让我下车,这些车牌可以提供某种程度的外交豁免权。
当领事馆的车驶入我居住和工作的狭窄巷道时,这一切就像间谍电影中的场景。我被告知,为了我的安全,我必须留在车里,而一名外交官则迅速进屋拿我的行李,幸运的是,我的行李在前一天晚上就已经打包好了。
当我们在车上等待时,一名戴着口罩、形迹可疑的人在巷子里走来走去,假装在打电话,显然他在监视我们。
我的邻居震惊而困惑的看着我,当我们开车离开时,我在车里向他们挥手告别,我知道这可能是最后一次看见他们了,真要告个别。
我在一个安全的地方度过了接下来的5天,驻上海领事馆的工作人员竭尽所能的让我感到舒适,显然工作人员仍在对此进行沟通,但我不清楚是否有任何进展。
我咨询过律师,也想过什么时候将此事告诉我的父母,但由于保密需要,我只能告诉极少数人,以防消息泄露,让情况变得更加复杂。
多年来,我一直抱怨外交贸易部的保密性,但现在我终于意识到,为了保护我们的安全,有必要不让其他记者看到这条新闻。
“现在开Julian Assange的玩笑还为时过早吗?”一名朋友打趣道,他指的是维基解密(WikiLeaks)的创始人,在厄瓜多尔驻伦敦大使馆工作了将近7年。

澳洲驻华记者Michael Smith卷入了一场戏剧性的国际事件(图片来源:AFR)
第二场戏
几天后,此事有了新的进展,外交贸易部和国家安全部达成了一项协议,这意味着Birtles和我可以离开中国,但条件是我们必须接受当面问询。
这是一个冒险的举动,因为需要我们信任中国当局,但令人感到欣慰的是,中国当局遵守了自己的承诺。当然,也没有其他选择。
周一下午,我在一名澳洲领事官员的陪同下,在上海浦东区嘉里酒店的31楼接受了对方问询,但领事官员不允许参与。
周三晚上,我的两个“朋友”在门厅见了我,并把我带到一个房间,那里还有另外两名警官。当我进入昏暗的走廊时,有一瞬间在想我是否还能出来。
问询持续了一个小时,他们礼貌地问了我一些基本问题,包括我待在中国的时间、我所报道的新闻种类、我与谁交谈过以及我与其他记者的关系。他们还问我是否认识成蕾,我的回答肯定让他们失望了,因为我们两人从来没有说过话。
谈话结束后,终于,我可以自由离开了。领事官员将我护送至机场,在那里,我见到了Bill和一支澳洲外交官小组。据悉,出境禁令直到面谈结束,在我们起飞前几个小时才被取消。
清关是最关键的时刻,移民官盖章发出的咚咚声,是我听到的最甜美的声音。我们在领事官员的陪同下,一路走到了登机口。
尽管起飞时我松了一口气,但在中国待了将近3年,这是一个令人失望的结局,我没有机会和朋友告别,也没有完成我一直在写的故事,甚至还有很多旅游景点没有打卡。

Michael Smith在悉尼酒店接受隔离(图片来源:AFR网站)
结束语
过去一周发生的事情,带来的问题比答案更多,我们仍不知道成蕾被拘留的原因,也不知道两名澳洲记者为何会有这般经历。
通常情况下,驻华的外国记者之所以成为目标,是因为他们写了令中国政府头疼的特别报道,但这起事件并不是因为这个。
有一种说法是,这只是另一种演习,目的是在澳洲政府站出来对抗北京的时候,可以“恐吓”澳洲政府。也有人称,不允许我们离开中国所带来的外交后果是不值得的。
据悉,这是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澳洲首次没有驻华记者。
周二早上,当我的飞机降落在悉尼时,这里阳光明媚的,我从未觉得这个城市能如此美好。讽刺的是,我现在正在接受另一种形式的“拘留”——14天的酒店隔离。但在中国,另一种选择可能更糟。
就在同一天,记者Bill Birtles也在ABC发表文章讲述自己接受调查及离开中国的经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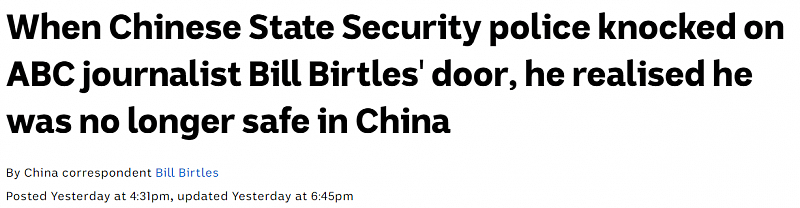
以下为全文翻译:
那是周三晚上,我感到压力非常、非常大。在北京公寓内,我和十几个朋友短暂告别,他们帮我收拾好在这里生活了5年的东西。
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发现很难一边招待朋友一边收拾行李,因为过了很久,行李箱还是空的。
根据大使馆的建议,ABC安排我搭乘早班从北京首都机场回澳。其实我不想离开,因为我感觉很安全,因为一切和往常一样。尽管最近有消息称,澳籍华裔记者成蕾因涉及国家安全而被拘留。
我曾经想过,ABC要求我们撤离是不是过于谨慎。但在一天午夜,有陌生人敲门造访,是7名国安部的警察。
我打开门看到两名身着制服的警察,一开始,我以为他们来是因为噪音扰民,之后我探出头发现后面还有5名便衣警察。
当时我就在想:“看来担心是有必要的。”当时的情景还留在我的脑海中——我的朋友们一直在“帮”我喝完剩下的酒,并请求警察不要把我带走,但很快我们就发现,他们的目的不是这个。
相反,警察向我展示了他们的身份证明,告诉我“涉及”一个案件,并称已对我下达出境禁令。他们还说,我在其它方面有“行动自由”的权力,第二天下午他们会通过电话进行问询,然后就离开了。
这是前所未有的经历,我从没听说过有外国记者会这样卷入国家安全事件。但敲门声带来的问题比答案多,如果你只是在传递信息,为什么要7名警察在午夜造访?又为什么要等到第二天下午呢?早上为什么不行?
虽然我不知道这些问题的答案,但收拾行李的事情看来要缓一缓了。第二天早上,我前往大使馆就此事寻求建议。

Bill Birtles
我的朋友,AFR记者Mike Smith也遭遇了类似经历,情况十分混乱。随着谈判的开始,我发现自己在北京进入了隔离状态,我可以看到和听到这个5年来被我称为家的城市,但却不能冒险出去。
日子一天天过去,我在大使馆内花了很多时间思考我是如何成为一枚棋子的,期间还会让朋友把我公寓的衣服和日用品拿过来。
我不想在任何虚假的东西上签字,也不想被用来指控他人。有人告诉我,无法百分百确保这次会面不是为了拘捕我。但一些经常与中国人打交道的澳人已经形成了这样一种观点,即中方至少在安排问询方面是真诚的。

今年早些时候,Birtles和Brant Cumming在韩国出现疫情后被迫在家隔离
在酒店房间内接受中国警方的问询
如果中国官员真的想利用一名澳洲记者让外交紧张局势升级,那天晚上可能就拘捕我了。我同意接受询问,但无论如何,我在北京的生活都无法恢复正常了。
第二天到了下午我才收到回应——显然中方缺乏紧迫感。询问地点是三里屯一家中档酒店,离我公寓不远处的热闹夜生活区。我不是一个人去的,但警察不许别人和我一起进去。
当我抵达时,我被带到22楼的一个房间。房间里有3名警察和一名翻译,还有一台摄像机对着我坐的沙发。旁边的小吧台放着一瓶酒和一些饼干,这原本是一间普通的酒店房间。
主事的是那个半夜敲我门的老警察,他操着浓重的北京腔对我说,我们想和你“聊一聊”。问询从最基本的问题开始——我的名字和工作,之后他们还问我做了多久驻华记者。
然后我被问及是否曾报道过有关新国安法的新闻以及我是通过哪些渠道获取的信息,不过他们都是点到为止,没有深入挖掘我的消息来源。

Birtles抵达澳洲(图片来源:澳洲广播公司)
警察有时还会开玩笑
之后,采访的重点转移至了可能与我有关的事件——涉及成蕾的国家安全案件调查。我认识她,但不是很熟,我肯定不是他们第一个问询的人。
我被告知,这次讨论与澳中关系有关,以及我对目前关系的看法。随着问询接近尾声,我的心开始变得踏实,这名老警察似乎不太喜欢回应我有关政治类的提问,并告知我中国是一个“法治国家”。
当他的一名同事打印问询记录时,他甚至开了几个玩笑。这份记录是全中文的,我仔细的浏览了一遍,以确保我不会在虚假的文件上签字。
内容为谈话的简略,描述精准,我在上面签了字,不过他们以法律原因为由拒绝我复印的要求。
我之后被带回大使馆,经过商议,尽管出境禁令在最后一刻出现了小插曲,但我还是有信心第二天能如约离开中国。
离开我称之为家的城市是什么感觉
我在北京工作了7年、作为ABC记者驻华5年,我对这样的结局感到十分失望和悲伤。遗憾的是,我不得不迅速与优秀的同事告别,他们经常忍受艰苦条件,一旦遇到困难,也没有别的国家可去。
悲伤的是,我被赶出去了,我成了外交纠纷中的一枚棋子。但我并不是唯一一个,今年早些时候,我的两名驻华记者朋友——《纽约时报》的Chris Buckley和《华尔街日报》的Phillip Wen也被迫撤离。
随着中美关系恶化,美国驻华记者也被迫撤离,而我的离开只是大势所趋,这将使澳洲、中国以及各国对彼此的了解和理解减少。
相关新闻:
担忧面临“任意拘捕”风险,澳洲驻华记者集体撤退!中方回应:询问属正常执法(组图)
(Joy)
专题:澳中关系降至冰点进入专题 >>
中驻澳大使:做好与澳新政府合作准备,聚焦共同利益以加强打击跨国犯罪(图)
澳中关系对双方都有利,最重要的是,它是建基于信任(组图)
中国大使回应澳政府禁用DeepSeek:过度解读安全风险,小院高墙只会导致自我孤立(组图)













 +61
+61 +86
+86 +886
+886 +852
+852 +853
+853 +64
+64


